閱讀〈羽毛〉
閱前告知,這是沒有甚麼計畫和考量,比較不考慮閱讀者的一個閱讀心得,他又長又碎,也不見得有甚麼價值,不過出於自己對這個短篇的熱愛,我還是想要寫出來,包含很多搖盪的見解,以及長長的原文,如果願意跟我一起讀著源問到最後,那你一定是很愛很愛我了。
之後還會再修正,我會加油的,吧?
0. 小小談論瑞蒙卡佛
羽毛是一篇瑞蒙卡佛的短篇小說,他是許多人推崇的一位短篇小說家,也是我所鍾愛的,且會想一再重讀的作者。他的故事總是在小心地營造日常性的同時,一邊展現著種種迫在眉睫的危機,在危機即將爆發時,又讓它被溫暖模糊的日常性淹沒。作品中所喚起的是不安的情感,在羽毛之中,這種不安隱隱約約,在各個生活片段中或加劇或減弱,不論怎麼變化始終都站在角色陰影當中。要能營造出深刻的不安感,想必他已然深刻的思量過一個問題,「生活究竟為甚麼成為了現在的模樣?」這樣光是提出就足以令人戰慄的疑問,他是如何準確把握住這個問題?為何他的故事總能刺激著讀者感到不安?或許就和村上春樹評論史蒂芬金時所說的那樣,出於絕望感。
「史蒂芬?金小說中的登場人物一面害怕那絕望的影子,一面在臨時的價值觀下尋求拯救的生活。許多時候,那就是男歡女愛,就是家庭。一開始,它看似有效地發揮功能。但絕望總是作為不可抗拒的超自然力量淩駕其上,即便借助愛也無法阻止這股力量。因為他們身上被與生俱來地打下了『絕望』的烙印。反過來說,他們只能通過絕望這一『拯救的缺失』,才能談論愛情?!?/div>
在瑞蒙卡佛的故事中,世俗敘事的價值如穩固的家庭結構、盡責堅毅的丈夫和父親、賢慧慈愛的妻子與母親、依據職能安穩守己的員工、忠貞不二的情感、在得到社會的合理安排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些全部都是短暫脆弱的價值。故事中的人物也不是從開始就質疑這些價值的存在,相反的,他們都努力追求或者維護過,可最終他們落敗了,他們屈服了,他們接過破碎殘缺的信念卻沒有辦法狠心丟棄,因為比起「沒有」價值,「可能有」價值的生活會比較安全點,虛偽的價值碎片或隱或現,他們一方面相信追求穩定生活是不顛的真理,一方面又感覺到自己珍視的生活是那麼脆弱易逝,掙扎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想法,生活依舊不停的進行,直到蘊藏的黑暗湧出,世界的光源被蝕去後,在只會越加黯淡的生活裡,被生活的浪潮一次次推向空寂的前方。
1. 閱讀筆記(附原文,整段長而瑣碎,新細明體是原文,標楷體和括號處代表筆記)
巴德和我在一個單位工作。有一天,他叫我和弗蘭一起去他家吃晚飯。我不認識他愛人,他也不認識弗蘭,兩下就算扯平了。不過,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裡有一個小孩,小孩應該有8個月大了。這8個月都跑到哪裡去了?這麼長的時間都他媽的去哪裡了呢?
(看似只是平常抱怨,但卻是奠定故事的曲調,歲月匆忙而空白,留下的的不比帶走的更多。)
我還記得那天巴德帶了一盒雪茄到班上,吃午飯的時候,在午餐室裡分給大家抽。是那種雜貨店裡賣的雪茄,「荷蘭大師」牌的。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條紅色標籤,包裝紙上寫著「是個男孩!」幾個字,挺顯眼的。我不抽雪茄,但還是拿了一根?!冈倌脙筛!拱偷禄瘟嘶螣熀袑ξ艺f,「我也不喜歡雪茄,是她的主意」。我知道他說的是他老婆,奧拉。
(暗示著巴德有新生男孩後,奧拉用雪茄分送眾人方式慶祝。
奧拉第一次出場,是藉由展現一個家庭主婦外交小手段的方式,巴德是較為木訥,而且有些微不自在,他不喜歡用分派雪茄方式高調告知他人嬰兒的事,對於新生兒,他的態度顯得有點不自在的疏離感。這是一個父親在外人面前提及孩子的感覺,突然從丈夫變成父親的身分轉變使他有點不自然。一個身分上的轉變,再這裡就埋下了伏筆。)
我從沒見過巴德的愛人,只有一次在電話裡聽過她的聲音。是個週六下午,無聊得很,便給巴德打了個電話,看他有什麼玩的計畫。是她接的電話,話筒裡傳來她的聲音:「喂——」我一下子有些發懵,一時想不起她的名字來了。巴德倒是跟我提起過幾回,但我總是一耳朵進一耳朵出。她又說了一遍「喂——」我能聽見那邊電視正開著。然後她問:「誰呀?」我聽見小孩開始鬧了。「巴德!」那個女人喊?!冈觞N了?」我聽見巴德的聲音。我還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電話掛了。後來在班上見到巴德,我沒提打過電話的事,不過,還是兜著圈子讓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笂W拉?!顾f。奧拉,我對自己說。奧拉。
(本來屬於男人的對話,無意間被一個陌生女人闖入,立場驟變,他發現是自己才是闖入者,而感受到孤立倉皇逃跑,這一種孤立的不自在感在之後一再出現強調。)
那天,我們在午餐室裡喝咖啡的時候,巴德跟我說:「沒什麼事,就我們四個。你和你媳婦兒,我和奧拉。沒什麼特別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點左右來吧。她六點喂小孩,之後弄孩子睡覺,咱們就吃飯。我們的地方不難找,這是地圖?!顾f給我一張紙,畫滿了線條,標示著大街小巷路口之類的,還有箭頭表示著東西南北的方向。一個大「X」子就是他家了。我說:「太好了,很期待的聚會啊?!共贿^,我發現巴德好像並不太興奮。
(聚會也可能是奧拉索提起,才讓巴德本身並不期待,他也不希望把兩個男人間的事情,變成兩個家庭的交流。
是他依然處在那份突如其來身分轉變的疏離感裡面。)
那天晚上看電視時,我問弗蘭去巴德那兒要不要帶點東西。
(極為迅速的切掉其他部分,轉到了他與妻子討論參加聚會的場景。
在讀者還無從得知女人是怎麼答應邀約之前,就先呈現了她即便答應了,也不太在意,些許抗拒的回答。)
弗蘭反問我:「比如說帶什麼?他說要我們帶什麼了嗎?我怎麼知道帶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她聳著肩,瞥了我一眼。
我跟她談過巴德的事,但她不認識他,也不大想認識他?!肝覀兛梢詭科咸丫迫??!顾f,「不過我無所謂。要不你就拿瓶酒吧?!顾α怂︻^,長髮搖擺在她肩頭。她似乎是在說,別人家的事,咱操什麼心呀?你惦記點兒我、我想著點兒你就行啦。
(芙蘭突然被捲進丈夫朋友的聚會裡,不自在來自於陌生的視線,還有不自主的感覺,眼前的穩定關係被他人闖入的不適,就如同前面男人闖入巴德家庭一樣,弗蘭被迫成為另一個闖入者。
這是從後面向前面補述的話語。)
「過來,」我向她擺擺手。她朝我這邊靠了一點兒,讓我一把能夠抱住她。弗蘭的金發散在背後,清新得像夏季裡的一杯飲料。我撚起她的頭髮,用力地聞,手纏繞在髮絲裡面。她讓我抱她,我把臉埋在她的頭髮裡,雙手抱著她。
頭髮會擋住她的眼睛時,她會很生氣,一邊把頭髮撥到肩後一邊抱怨:「這頭髮真是一堆麻煩。」弗蘭在一家奶品廠工作,上班時要把頭髮盤起來。每晚回家都得洗一次頭,然後邊看電視邊不停地梳理。偶爾她也會威脅說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會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歡她的頭髮,她知道我對她的頭髮喜歡得都有點兒瘋狂了。我對她說過我就是因為她的頭髮才愛上她的。我告訴她,如果她剪了頭,說不定我就不愛她了。有時我會叫她「瑞典人」,因為瑞典人都有一頭金髮。「瑞典人」這個外號,她還能湊活地接受。在那些我們在一起的晚上,她會一邊梳著她的長髮,一邊和我一起大聲地說出我們希望擁有的東西,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的東西。比如一輛新車,那曾是我們的願望之一。我們也曾盼望過能一起到加拿大玩兩個禮拜。但從來沒有盼過的一個願望,就是孩子。我們還沒有孩子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想要孩子??赡芤葬釙胍桑覀兓ハ噙@樣說過。反正我們現在不想要,等以後再說吧,以後什麼時候呢?我們想我們可能就這樣一直等下去了,一直等到以後。
有時晚上我們會去看電影,要不就待在家裡看電視。有時弗蘭會為我烤些吃的東西,不管烤什麼,烤得怎麼樣,我們都會一口氣吃完。
(日常生活中的虛假與偽裝,不管是真的承諾,還是假的願望,都有一個期限,那個期限是一段空白,過了那段空白後,東西在肉眼不可見的方面,漸漸腐壞消失。
這是對於那段空白的補述,對於深愛的人,許以承諾,編織願景,用以填充空白,而那些也只是填充罷了,生活就是一片被遺留下來的巨大虛無。
面對虛無,海明威會指著它說,「這就是虛無。」,而瑞蒙卡佛的方式更加入世一點,他會說,「等到以後再說吧?!?/font>
呈現出一個日常的家庭活動,看電影或者看電視,吃點甚麼東西,或者喝葡萄酒,這樣子等到以後。
在最後埋下一個值得引爆的炸彈,他們現在對於孩子興趣缺缺,想要先順其自然,他們甚至都不相信將來會想要。)
「他們可能不喝葡萄酒?!刮艺f。
「就帶葡萄酒吧?!垢ヌm說,「要是他們不喝,那咱們就自己喝」。
「白的還是紅的?」
「再帶點兒甜品?!顾龥]搭理我,「不過,帶什麼都行,我真的無所謂。巴德是你的朋友,這是你的聚會。咱們可別太當回事,小題大作的,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做個覆盆子咖啡蛋糕吧,或者什麼別的點心?!?/div>
「他們會準備點心的?!刮艺f,「你不會請人到家裡吃飯而不做個飯後甜點的?!?/div>
「他們可能做個大米布丁,哦,甚至果子凍之類的我們不愛吃的東西?!顾f,「我都沒見過那個女的,怎麼知道她會做什麼?如果她給我們吃果子凍怎麼辦?」
弗蘭搖著她的頭。我聳了聳肩。不過她說得有道理。
「那些巴德給你的老雪茄——」她接著說,「帶上點兒。那樣你們就可以飯後到客廳去抽點雪茄喝點葡萄酒,就像電影裡那些人那樣?!?/div>
我說:「行,那就帶上咱們自己的點心。」
弗蘭說:「咱們就拿一條我做的麵包吧」。
(金色長髮、電影生活,包圍他們夢想的,是一種被外在形塑的夢想生活。
他們的、我們的,對話裡用他和我分別了不同生活的兩個家庭:他們不喝我們喝、你的朋友、你的聚會、他們會準備點心、他給我們做不想吃的點心、我們自己帶點心、我做的麵包。
對話中構築出的關係不外乎我和你、我們與他們。)
巴德和奧拉住在離城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我和弗蘭在這兒已經住了三年了,唉,卻還沒怎麼在這邊的鄉間兜過風。車子開在這些蜿蜒小路上的感覺真好。剛剛傍晚,天氣又好又暖和,我們看見了牧場,柵欄,還有正向著老畜棚踱步的奶牛。我們看見了柵欄上黑色的山鳥長著紅色的翅膀,鴿子繞著幹草棚兜圈子。還有花園之類的,野花盛開,一幢幢小房子躲開大路遠遠的待著。
(對話結束後,緊接著兩人已在路上,他總是勇於裁減不夠強力相關的場景。在得知消息的那天,從上班到遇到巴德,巴德分送雪茄,邀約男人來家庭聚會,回到家中與妻子談論參加事宜,在出發前事情,連續的時間只被留下幾個片斷,小心地維持著日常景觀,以及其中潛伏的不安定感。)
我對弗蘭說:「咱們要是能在這兒有個房子就好了?!怪徊贿^是隨便想想,只不過是又一個不會實現的願望吧。弗蘭沒有答話,她正忙著看巴德給的那張地圖。我們開到了一個他標示該出去的路口,然後按照地圖說得那樣右拐,又開了整好英里。路左邊,我看見了一片玉米地,一個郵箱,還有一條長長的砂石鋪的車道。車道的那一頭,幾棵樹後面是個帶門廊的房子,房頂上有根煙囪,因為是夏天,當然沒有煙嫋嫋升起。不過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景象,對弗蘭說了我的感覺。
她卻對我說:「那只不過是些樹杈子。」
(再次說出能夠麻痺彼此的願望時,女人被即將到來的緊張束縛著,因此沒有回應。隨後她貶低了眼前的景象,延續了從出發以來的不安定感。
如之前所言,兩人其實對於願望不會實現有著清楚的認知,在即將到達巴德住所前,他又隨口說出了空白的願望,也是他在故事裡最後一個和故事主線無關的空想,接下來將會遇到不再是空想而是確實可能的景象。)
我把車拐了進來,車道兩旁都是玉米,長得比車還高。我能聽見下麵砂石嘎紮嘎紮地咬嚼輪胎的聲響。把車開到房子跟前之後,我們看見了一個花園,裡面的藤蔓上掛著些綠色的東西,籃球般大小。
「那是什麼玩意?」我問。
「我怎麼知道?」弗蘭說,「可能是南瓜。不知道!」
「哎,弗蘭,」我說,「放鬆點兒?!?/div>
她什麼話都沒說,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又鬆開了。車開到房子跟前時,她關上了車上的收音機。
前院裡立著一個嬰兒搖籃,幾件玩具散放在門廊下。停車的時候,我們忽然聽到了可怕的嚎叫聲。對,沒錯,屋子裡面有個會啼哭的嬰兒,不過那聲響可真夠沖的,對於一個嬰兒來說,音量未免是過於高了。
「什麼聲音?」弗蘭問。
誰想這時一隻像禿鷹一樣大小的東西從樹上重重地拍打著翅膀飛下來,直衝衝地落在車前面。它渾身顫抖,伸著長長的脖頸扭向車這邊,抬起頭,打量著我們。
「該死的!」我說著,呆坐在車裡,雙手放在方向盤上,凝視著那個傢伙。
「你能相信嗎?」弗蘭對我說,「我以前還從沒見過一個真的呢」。
我們當然都知道那是只孔雀,但我們誰都沒說出聲。我們只是看著它,看著它昂頭伸向空中,又粗糙地大叫了一聲。它的羽毛乍楞起來,弄得它整個身子比剛才落下的時候大了一倍。
(因為孔雀的出現,女人對房子的敵意轉為好奇,反而男人卻顯得厭惡,孔雀聲音像是嬰兒的哭嚎,男人下意識想趕走牠。
這是整個故事裡最奇特的地方,孔雀出現在故事的前面,不是在最後,而是在開始就出現的謎語。)
「該死的!」我又說了一次。我們坐在車的前座上一動沒動。
孔雀又向前移動了一點,頭側向旁邊,繃著勁兒,明亮而充滿野性的眼睛一直盯著我們。尾巴翹起來,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伸展開,閃爍著彩虹上有的每一種顏色。
「天哪!」弗蘭小聲地說,手放到我的膝頭。
「該死的!」真沒什麼別的可說的了,我只能又罵了句。
孔雀又發出了那哀號的聲音:「喵嗷,喵嗷!」要是在深夜裡、又是第一次聽見這動靜,我真會以為是什麼人要死了,或是什麼瘋狂而危險的東西走過來。
(有著華麗外表同時,卻會發出悲慘垂死的聲音,這樣的綜合所指是甚麼?)
前門開了,巴德一邊系著襯衣扣子,一邊走到門廊上。他頭髮濕著,像是剛沖完淋浴。
「閉嘴,喬伊!」他對那只孔雀說,又沖著它拍了拍手。那傢伙向後蹭了蹭。「夠了。這樣就對了,閉上嘴。你這個老壞蛋,閉嘴!」巴德走下樓梯,邊朝車這邊走過來,邊把襯衣塞到褲子裡面。他穿著他上班總穿的衣服──藍牛仔褲和粗斜紋的棉布襯衣。我穿著便褲和短袖運動衫,還有一雙不錯的平底鞋。看了巴德的穿著,我有些不高興,自己出門前過於當回事地打扮了一番。
(巴德更加漫不經心,而他對待孔雀的態度似乎對它習以為常,孔雀在這裡像看門寵物一樣。)
「很高興你們能來,」巴德走到車旁說,「來,進來吧」。
「哎,巴德。」我沖他打著招呼。
弗蘭和我下了車。那只孔雀向一旁挪了一點,猶豫不決地搖閃著它的腦袋,一副壞相。我們小心翼翼地和它保持著距離。
「還好找嗎?」巴德問我。他沒有看弗蘭,等著我來介紹。
「你給的方向很好找。」我說,「哎,巴德,這是弗蘭。弗蘭,這是巴德。你的事她可都知道呢,巴德」。
他笑了,和弗蘭握了手。弗蘭比巴德高,巴德看她需要向上抬點兒頭。
「他經常提起你?!垢ヌm邊說邊把手撤了回來,「巴德這個,巴德那個的。在這裡,你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似的,成天價說,說得我感覺像早就認識你一樣了」。她一邊說著,一邊留神看著那只孔雀。孔雀正向著門廊這邊靠近。
「這就是咱哥們兒!他就應該念叨我!」巴德說完,朝我咧嘴笑了笑,又輕輕打了我胳膊一拳。
弗蘭一直拿著她的那條麵包,局促得有些手足無措。她把麵包遞給巴德說:「我們給你們帶了點兒東西來?!?/div>
(兩人的微妙距離從身高上先顯現出來,小心的應酬對話。巴德與男人的互動,更讓女人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巴德接過麵包,翻過來看了看,就像那是他見過的第一條麵包似的。「你們太客氣了?!拱偷掳腰I包舉到臉旁,使勁地聞。
(接下來巴德與弗蘭間的互動,總是透著過度的反應。就和男人當時打電話卻遇上奧拉的情況相似。親近的人所有的另一個親近者,對於自己來說是一道橫加阻攔不可名狀的牆。)
我告訴巴德:「是弗蘭烤的麵包」。
巴德點了點頭,說:「走,我們進去吧,見見我老婆,孩子他媽」。
他當然是在說奧拉。這兒只有奧拉是個母親。巴德告訴過我他自己的母親已經去世了,爸爸在他還很小的時候也離開了他。
(提到了母與子,而芙蘭心底可能有蘊含這種關係的建立。
孔雀在這場景裏頭扮演著奇怪的角色,像是另一個孩子一樣,又像是另一種生活的象徵,而這個可能是兩人彼此空許諾時提出的一個想像。)
巴德開門的時候,孔雀噌的一下躥到我們的前面,跳上門廊,它也想進屋裡去。
「??!」孔雀擠到弗蘭腿上時,弗蘭叫了一聲。
「喬伊,該死的!」巴德說著,重重地打了孔雀的前額一下??兹冈陂T廊裡後退了幾步,搖擺著身軀,尾部的翎毛發出哢啦哢啦的聲音。巴德裝出要踢它的樣子,孔雀又向後退了退。巴德幫我們開門時說:「奧拉總把這個該死的東西放進屋。過不了過久,它就要到他媽的桌子上吃飯,到他媽的床上睡覺了。」
一進屋,弗蘭就站住了,回過身看著門外的玉米地。「你這地方真好!」她說。巴德還扶著門,說道:「是啊,是挺好的,你覺得呢,傑克?」
「當然啦?!刮覜]想到弗蘭會突然這樣說
(對於剛才還心懷排斥的女人,突然說出讚美的話語,因為孔雀的出現,讓她稍微釋懷,儘管誇讚的還不太自然,包括後面不倫不類的話語)
「這種地方也不都像你們誇的那樣好?!拱偷抡f著,仍舊扶著門,向孔雀做出一個威脅性的動作,招呼我們說:「快走快走,慢一下都不行。快請進,夥計們」。
我指著窗外問:「哎,巴德,那裡種得是什麼呀?」
「番茄?!拱偷禄卮?。
「咱們的農民很有一套啊!」弗蘭搖晃著腦袋說。
巴德笑了。我們進了屋,客廳裡一個小個子的豐滿女人正等著我們,頭髮盤成了一個圓髻,手揣在圍裙兜裡。她滿臉通紅,讓我以為她可能是喘不過氣,或是在生誰的氣什麼的。她掃了我一眼,目光就移到弗蘭身上。不是那種冷淡的眼神,只是一個勁地盯著弗蘭看,臉繼續泛著紅。
(從開頭就被提及的奧拉出現,以一種相當居家,樸素而戒備的方式出現。弗蘭與他正好相反,根據登場時的敘述,一頭金色長髮,還多少有點叛逆少女氣質,她認為芙蘭是比她美貌有優勢的女人。)
「奧拉,這是弗蘭。這是我朋友傑克,我總和你說起的那個傢伙。夥計們,這是奧拉?!拱偷逻呎f邊把麵包遞給了奧拉。
「這是什麼?」她說,「啊,自家做的麵包,太好了,謝謝。隨便坐吧。別客氣。巴德,你還不問問人家想喝點兒什麼。我爐子上正做著東西呢。」奧拉說著,拿著麵包走回了廚房。
「請坐。」巴德說。弗蘭和我撲撲通通地坐在沙發上。我找著我的香煙?!高@有煙灰缸,」巴德說著從電視機的頂上拿下了個很沉的東西?!赣眠@個?!顾呎f邊把那東西放到我面前的咖啡桌上,是那種做成天鵝模樣的玻璃煙灰缸。我點了煙,把火柴扔到天鵝背上開的口子裡,看著一縷細煙從天鵝身子裡飄出來。
(夫妻兩都期待著生活上的變化,男人也好奇著朋友的夫妻生活,玻璃天鵝的煙灰缸,恰如此種飄忽幻想與實際塵土的集合)
彩色電視正開著,我們就看了一會兒。螢幕上,幾輛賽車撕裂在賽道周圍,播音員的語調既沉重,又像正隱瞞著什麼令人興奮刺激的消息?!肝覀冞€要等正式的官方確認……」播音員說。
「你們想看這個嘛?」巴德問。他還站在那兒。
我說我無所謂。我是真的無所謂。弗蘭聳了聳肩,像在說,看這個還是別的,對於她都沒區別。反正今天就這樣交待了。
「就差最後的20多圈了?!拱偷抡f。「現在賽道已經封了。剛才的撞車事故可真嚴重,半打車撞到了一起。幾個司機受了傷,還沒說傷得有多重。」
「別換了,」我說,「咱們就看這個吧」。
「說不定真有輛車會他媽的在我們眼前爆炸呢。」弗蘭說,「要是沖到看臺上才來勁呢,撞翻那個賣油晃晃的熱狗的傢伙!」她的手指間夾著一縷頭髮,眼睛盯在電視上。
巴德看了看弗蘭,看她是否在開玩笑?!改莻€撞車可真是夠厲害的。一個接一個的。車,車的零件,還有人,飛得到處都是。好啦,你們想喝點兒什麼?我們這兒有麥芽酒,還有瓶‘老烏鴉’?!?/div>
(巴德講述著乏味的話語,想沖淡眼前略顯尷尬的事故場面,女人則講述出戲劇化的發展,期待著遇上甚麼驚奇的事情,或者說她想要藉著討論血腥陽剛的話題,試圖融入到巴德的談話中。女人僅靠著想像,推測出巴德這樣男人會喜歡的發展,但是當獨自觀看禁忌的事物的刺激感,被他人闖入後,那種刺激也就只剩下亟欲擺脫的不安,於是他很快找到藉口擺脫了對方。
如白噪音裡描述的,聚在電視前一起觀看遠處危險的奇蹟,就是現代家庭具有儀式感的日常。)
「你喝什麼?」我問巴德。
「麥芽酒。又涼又好喝?!?/div>
「那我也喝麥芽酒。」
「我來點兒‘老烏鴉’,再來點兒水吧」,弗蘭說,「放在一個高玻璃杯裡,行嗎?來點冰。謝謝啊,巴德」。
「行?!拱偷抡f。他又瞥了眼電視,就進廚房了。
弗蘭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沖著電視的方向努了努嘴。「看那上面?!顾吐曊f,「看見了嗎?」我看了過去,電視機上邊,放著一個細長的紅色花瓶,瓶子裡插著幾枝雛菊?;ㄆ颗赃叺淖啦忌?,坐著一個熟石膏塑的牙齒模型,那該是世界上最參差不齊的牙齒模型了。這個噁心的傢伙上面,既沒有嘴唇,也沒有下巴,就那幾顆老石膏牙,塞在一塊厚厚的像黃色口香糖的東西上。
(女人第一眼注意到了醜陋奇特東西,稍微對應著她對暴力場景的期待。
孔雀、電視節目、還有嚇人的牙齒模型,男人的反應可以看出是厭惡、無所謂、還有噁心,但在女人反應裡卻有著其他的複雜情感,兩人的剛開始對好惡的一致性,正一步步被埋下差異的種子。)
就在這時,奧拉拿著一罐果仁和一瓶啤露走出來,圍裙已經脫掉了。她把那罐果仁放在咖啡桌上的天鵝旁邊,沖我們說:「自己拿啊。巴德正給你們拿飲料呢。」說這話時,奧拉的臉又紅了起來。然後,她坐到一個老藤條搖椅上,晃悠了起來。她邊喝著啤露,邊看電視。巴德拿著個小木質託盤走出來,上面放著弗蘭要的威士卡和水,還有我和他的兩瓶麥芽酒。
「要玻璃杯嗎?」他問我。
我搖了搖頭。他輕拍一下我的膝頭,轉向了弗蘭。
(巴德相當習慣於朋友間的肢體接觸。)
弗蘭接過玻璃杯,說了聲:「多謝。」又開始盯著那些牙齒看。巴德也順著她看的方向看過去。電視裡,賽道四周,車在嚎叫。我拿起麥芽酒,注意力集中在螢幕上,牙齒可不關我的事。
(男人感覺到無禮,但他並未試圖阻止或轉移話題,而是想要置身事外,如今弗蘭從一個抗拒聚會的旁觀者,再從一名被迫闖入者的身分,漸漸被這屋裡的種種痕跡拉入事物的核心。反而男人以當初意外通過通話聽到奧拉聲音,知曉自己是闖入者的不自在感,冷漠地把自己放逐到生活之外。)
「那是奧拉整牙前牙齒的模樣?!拱偷聦Ωヌm說,「我已經習慣它們了,不過我猜,它們擺在那上面,看起來挺可笑的吧。天知道她為什麼還要留著這玩意兒!」他看了看奧拉,又看著我,沖我眨了眨眼。他坐在「懶蟲」躺椅上,翹起二郎腿,邊喝著麥芽酒,邊盯著奧拉。
奧拉的臉又紅了。她握著酒瓶,喝了一口,然後說:「留著它們,是為了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什麼」。
「什麼?」弗蘭問。她本來正翻弄著那罐果仁,想找點兒腰果吃。弗蘭停了下來,看著奧拉。
「不好意思,我沒聽清。」弗蘭看著那個女人,等著她說話。
奧拉的臉又一次紅起來?!肝矣泻芏嗍露荚摳兄x他?!顾f,「這牙齒就是我要感謝的事情之一。留著它們是要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多少?!?/div>
她喝了一口啤露,放下瓶子對弗蘭說:「你的牙很漂亮,弗蘭。你一進門我就注意到了。但我的牙,我小時候,它們全是壞的,咯咯棱棱的?!顾弥讣浊昧饲们懊娴膬深w門牙,接著說,「那時我爸我媽沒錢給我整牙。我的牙只能生下來什麼樣就什麼樣。我的前夫也不關心我的樣子。對,他不管。他唯一關心只是他的下一瓶酒從哪裡來。他在世界上只有一個朋友,就是他的酒瓶子?!顾龘u著頭,「後來巴德出現了,把我從那堆亂攤子裡救了出來。我們在一起後,巴德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得把這些牙修理修理。’那個鑄型就是在碰到巴德後不久,在我第二次去見整牙醫生時做的,就在裝上整牙支架之前。」
奧拉的臉一直紅著。她看著電視,喝著啤露,似乎再沒什麼要說的了。
(奧拉牙齒矯正的意義,與弗蘭留長髮的意義似乎有所相通。
巴德與奧拉因矯正產生的連結,比起弗蘭為了取悅男人留長髮的行動似乎更有重量。巴德協助奧拉一起改變了甚麼,奧拉留下了模型,以此紀念當時做出的改變。這正是男人與女人渴望,卻遲遲沒有付諸行動的,在生活留下有意義的痕跡,如果沒有這樣的痕跡,他們就生活在一片空白中,至少目前他們能用電影、電視、烤雞、如瀑的燦金秀髮來填補空缺。)
「那個整牙醫生肯定是個天才!」弗蘭邊說,邊看著電視機上面那排像是恐怖表演一樣的牙齒。
「那醫生確實好極了!」奧拉說著轉過身來,「看見了嗎?」她張開嘴,又給我們展示了一遍她的牙齒,這次她一點兒也不害羞了。
巴德早已經走在電視機的前面,拿下了牙齒,走到奧拉身邊,把它們放到奧拉的臉頰旁?!缚?,整形之前和整形之後?!拱偷抡f。
奧拉起身從巴德手裡拿下那排牙齒。「你知道嗎?那個整牙醫生本來想要自己留下這個的?!顾f話時,把那排牙齒放在了腿上,「我說不行,我提醒他,它們可是我的牙。所以他只能給這個鑄型照了張照片。他告訴我他要把照片發在雜誌上。」
巴德說:「想想那會是本什麼樣的雜誌吧。我琢磨著沒什麼人要看那種東西吧?!?/div>
(因為牙齒的話題,化解初始到現在的尷尬氛圍。
巴德夫婦從牙齒矯正開始,似乎在向男人和女人展現他們的家庭,一個穩定而有明確意義的概念,一個在世俗上更加成熟的家庭模型。
而男人的家庭相比較下,核心匱乏感慢慢加深了,剛開始弗蘭對巴德家的厭惡感,難道不是因為她徹底的不認同一個定了型,生活重複而缺少變化的家庭感嗎?)
我們都笑了。
「等摘下了整牙支架,我笑的時候總還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就像這樣——」奧拉說,「現在我有時還這樣做。習慣嘛。有一天,巴德說,‘你不用那樣捂嘴了,奧拉。像這樣漂亮的牙齒,你可不用把它們藏起來。你現在的牙齒很好了?!箠W拉看著巴德時,巴德沖她擠了擠眼。她微微一笑,低下了頭。
弗蘭喝著她的飲料,我也喝了點兒麥芽酒。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弗蘭也一樣。但我知道過一會兒弗蘭可會有很多要說的了。
我說:「奧拉,我有次打電話過來,你接的電話,但我給掛了。我也不知道我當時為什麼就給掛了?!刮艺f完,吸了口麥芽酒。我也不知道這時候我為什麼要提起這件事來。
「我不記得了?!箠W拉說,「那是什麼時候?」
「有一陣子了?!?/div>
「我不記得。」她搖著頭說,用手指擺弄著腿上的牙齒模型,看著賽車比賽,又把椅子搖動起來。
弗蘭看著我,咬了咬下嘴唇,但沒有說話。
(隨著話題拉開,原本的顧慮也被說了出來。
出現在這裡,有點前嫌盡釋的舒緩,彷彿在把原先格格不入的線頭都匯集成融洽。但女人此刻卻發現男人那祕密的經驗,不安了起來。原來只有兩人世界的家庭生活也不是那麼的毫無保留,她或許有這樣的想法。)
巴德說:「怎麼樣,還有什麼別的新鮮事說說?」
「再吃點兒果仁呀,」奧拉說,「晚飯馬上就好了。」
裡屋傳來了哭聲。
「可別是他!」奧拉對巴德說,做了個鬼臉。
「那個小傢伙……」巴德說著向後靠在椅背上。我們看完了剩下的比賽,又跑了三四圈的樣子,沒有聲音。
我們又聽見一兩次嬰兒的哭聲,令人焦躁地從屋子裡面傳出來。
(從開頭就揭示的新生兒又出來承接劇情發展。就在巴德夫婦剛展示完假牙的故事之後,提醒這個故事的核心事件會是嬰兒,牙齒模型不過是恰到好處的鋪墊。)
「怎麼搞的?」奧拉說著站了起來,「什麼都準備好了,就等著大家入座了,我只要再把肉汁調好就行了。這傢伙又鬧起來了,我還是先進去看看孩子吧。你們大家幹嘛不過去入席呢?我馬上就來?!?/div>
「我想看看孩子。」弗蘭說。
奧把手裡還拿著她的牙。她走過去把它們重新放回到電視機上,然後說:「這小傢伙剛才可能是著急了,他還不太習慣見陌生人。等等看我能不能哄他睡著了,他睡著的時候,你們就能去看了?!拐f完走向門廳邊的房間,打開門,輕輕地走進去,帶上門。嬰兒不哭了。
巴德關上電視,我們走進餐廳,坐在餐桌旁邊。巴德和我談論起工作上的事,弗蘭聽著,不時會問個問題。但我能看出她已經膩煩了,也可能是因為奧拉沒讓她看嬰兒,生了氣。她隨便流覽著奧拉的廚房,翻翻奧拉的東西,手指纏繞起發梢。
(男人敏銳的察覺到嬰兒對女人產生的影響,她想要在這段一直落空的許諾中找到一絲真正可靠的痕跡。她翻看奧拉的東西,手指玩弄著髮梢,似乎這是兩人唯一可以做為抵抗滿屋子家庭痕跡的連結一樣。)
奧拉回到廚房裡時說:「我給小傢伙換了塊尿布,還給他一個橡皮鴨子玩。他可能能讓咱們安心吃飯了,不過也說不準。」她說著,打開烤箱門,從裡面拿出個平底鍋,然後往碗裡倒了一些紅色的肉汁,把碗放在桌子上,接著又打開幾個盆盆碗碗的蓋子,看起來是一切就緒了。桌子上有烤火腿,甜土豆,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子,和蔬菜沙拉。弗蘭的麵包擺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邊。
(女人的麵包擺在了主菜的位置。奧拉憑藉細微的動作無形又讓弗蘭更放鬆戒備,更願意進入他們家庭氛圍之中。)
「我忘了拿餐巾紙。」奧拉說,「你們先吃。想喝點兒什麼?巴德吃飯時總喝牛奶。」
「牛奶好啊?!刮艺f。
「我來點兒水吧?!垢ヌm說,「我自己拿吧,你已經夠忙的了,就別再費心來照顧我了?!顾妨饲飞?,想要站起來。
奧拉說:「沒事,你們是客人嘛。坐著吧。我去拿?!拐f著這話時候,她的臉又紅了。
我們只好坐下來,手放在膝蓋上等著。我的腦子裡想著那些石膏鑄的牙齒。奧拉帶回了餐巾紙,還有給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給弗蘭的一杯冰水。弗蘭說了聲:「謝謝?!?/div>
(當男人發呆時,他想到的是牙齒模型,但並沒有想得很深,也沒有給出評價,就像是剛好提及。或許這個為伴侶付出的小故事,在他心裡留下了個行動草綱。)
「別客氣?!箠W拉說著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頭做飯前的禱告。他的聲音很低,我幾乎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但大概意思我還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謝上蒼賜給我們正要消滅掉的食物。
「阿門!」巴德禱告完時,奧拉也這樣說了一句。
巴德遞給我盛火腿的盤子,自己來了點兒土豆泥。我們埋頭地吃起來,除了偶爾我或是巴德會說句「這火腿真不錯」、「這甜玉米是我吃過的最好的甜玉米」以外,大家幾乎沒說話。
「麵包做的很特別。」奧拉說。
「請再給我來點兒沙拉吧,奧拉?!垢ヌm說,聲音好像變得更柔和了一點。
「再吃點兒這個?!姑看伟偷逻f給我火腿或是紅肉汁時都會這樣說。
(在奧拉的熱情招待,還有對女人麵包的重視之後,女人對這裡顯得不再緊張。相比於巴德,奧拉更能理解運用細微動作安撫女人,巴德則是大咧咧將食物遞給男人,用粗野的方式表現男人之間的情誼,兩種截然相反的應對方式營造出兩種質地類似的情感。)
不時,我們還會聽見嬰兒哭鬧的聲音。奧拉會側過頭去聽,確定沒什麼大事後,滿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如果沒有前面女人的心裡鋪墊,這只會是個很乏味不值一提的日常描寫,然而這個間奏在一段鋪墊後,讓人對嬰兒的出場與女人的互動有了足夠的期待感。)
「小孩今晚有點兒不高興了?!箠W拉對巴德說。
「我還是想看看他?!垢ヌm又提出來,「我姐姐也有個小孩,不過他們住在丹佛,離著太遠。我什麼時候才能夠去一趟丹佛呀?這個外甥,我到現在還一直沒見過呢?!垢ヌm停下來想了想,然後繼續吃起來。
(她停下來想了想,和前面想看小孩的念頭成了一串思緒,但是為甚麼她那麼想要個孩子?孩子於她代表了什麼樣的意涵?是美好?是兩人關係的象徵?還是她所想要的變化?不論如何,孩子的真實面貌都將要揭曉。)
奧拉用叉子叉了點兒火腿,對弗蘭說:「等會兒吧,等他趕快睡著了吧。」
巴德說:「這菜還都剩著好多呢。來,大夥再吃點兒火腿和甜土豆?!?/div>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蘭說著把叉子擱在盤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是不能再吃了?!?/div>
「留著點兒肚子,」巴德說,「奧拉還作了大黃派呢。」
弗蘭說:「你們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塊就足夠了?!?/div>
我說:「我也吃一小塊。」其實,說這話只是客氣客氣。13歲那年,我曾就著草莓冰淇淋吃大黃派吃得生了病,從那以後,我就開始討厭大黃派了。
(在男人與弗蘭出發前,就曾討論過遇上主人端上不喜歡吃的東西時,他們會有多麼不開心,但現在事情發生後,男人似乎也沒有特別不快的念頭,而是隨意應付罷了,從抗拒到安然接受的轉變弧線十分理所當然。
為甚麼這裡提到從過往開始就相當厭惡大黃派的往事?是不是他現在依然還是保留著13歲少年般的心境,看待生活裡發生的事情?他與弗蘭對於將來的迷茫與故作豁達,不就是少年心境的體現嗎?)
我們吃光了自己盤子上的東西後,又聽見那只該死的孔雀的動靜。這次,那個傢伙跑上了房頂。聽得出來,它就在我們的頭頂上,在木瓦上走來走去,弄出滴答滴答的聲響。
巴德搖著頭說:「喬伊馬上就會停下來的,它一會兒蹦累了就去睡覺了,就睡在那些樹上」。
孔雀又發出了那種嚎叫:「喵奧——」誰都沒說話。有什麼可說的呢?
(這一刻的沉默,提示剛開始的奇妙動物還在外頭醞釀著,蓄勢待發,而牠終將進到屋裡,發揮某種作用。)
奧拉沖著巴德說:「它是想進來,巴德」。
「哼,它不能進來!」巴德說,「如果你沒注意到的話,我提醒你一下:我們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只該死的鳥坐在一起。那只髒鳥,還有你的那排舊牙!人家會怎麼想?」他搖著腦袋,笑了。我們都笑了。弗蘭也和我們一起笑。
「它不髒,巴德?!箠W拉說,「你是怎麼了?你不是挺喜歡喬伊的嘛。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它髒了?」
「就從那次它在咱們的毯子上拉屎開始,請原諒我這不雅的語言?!顾麑Ωヌm說,「我得跟你說,有時我真想掐死這個老傢伙。不過它都不值得一殺,是不是,奧拉?有時,大半夜的,它的叫聲能把我從床上提摟起來。它現在連個屁都不值,是不是,奧拉?」
奧拉對巴德的廢話搖搖頭,又盛了點兒青豆放到自己的盤子上。
「你最開始是從哪兒弄來這個孔雀的?」弗蘭想知道。
奧拉抬起頭說:「我一直想養只孔雀。小時候在雜誌上看到過一張孔雀的照片,我就覺得那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東西。我把那張照片剪了下來,貼在我的床頭,保留了很長時間。後來等我和巴德有了這個地方後,我覺得有機會了。我說,‘巴德,我想要一隻孔雀。’那時巴德還嘲笑我呢」。
(「你甚麼時候開始覺得它髒了?」
假使這隻孔雀象徵的兩人之間的關係,就顯得格外殘忍,而似乎也是如此,牙齒模型代表女人對男人的感激,孔雀則是從小時候在雜誌看到,她所認為最美麗的東西,雜誌上歌頌最美的事物,無非就是愛情,抑或者婚姻。
男人對此開玩笑地奚落,女人不顧他人眼光珍惜,但它時常不受控制,有時會把生活弄得一蹋糊塗,但兩人習慣有它在。
然而,習慣有它在,就等於不會失去它嗎?)
「不過我還是到處幫她打聽來著,」巴德說,「我聽說鄰村裡的一個老傢伙養這東西。他管它們叫天堂鳥。為了這只天堂鳥,我們花了一百塊?!顾呎f邊打了一下自己的額頭,「上帝,我可給自己找了個品位昂貴的女人呦。」他沖奧拉咧著嘴笑。
「巴德,」奧拉說,「你自己都知道這是瞎說。不說別的,喬伊至少是個好的看門的?!顾龑Ωヌm說,「有了喬伊,我們就不用養狗了。它什麼都能聽得見」。
「要是等我們過不下去了,很這可說不準啊,我就把喬伊給燉了,」巴德說,「連著毛一鍋燴」。
「巴德!這可不是好開玩笑的,」奧拉說,但她自己裂開嘴也笑了,讓我們又一次好好欣賞了一次她的牙齒。
小孩又開始折騰了,這次聽起來哭得很兇。奧拉放下餐巾紙,從桌子邊站了起來。
巴德說:「他真是沒完沒了。把他抱出來吧,奧拉?!?/div>
「我也正想這麼著兒呢?!箠W拉說著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悲歎了一次,我脖子上的汗毛都豎起來了。我看了弗蘭一眼,她把餐巾紙拿起來,又放了下去。我朝廚房窗戶那邊看了看,外面已經黑下來。窗戶敞著,窗框上還有一層紗窗。我覺得鳥的聲音是從前門廊那邊傳來的。
(男人聽到孔雀悲嘆,女人似乎想離開座位,又停了下來,兩人在這聲音中,感應又回到了一致中,在這聲驚訝過後,人們等待孩子出現,這聲音分明是揭開悲劇的預言。)
弗蘭扭過頭看著門廳,等著奧拉和那個嬰兒。
過了會兒,奧拉抱著孩子走出來。我看了一眼,深吸了口氣。奧拉坐在桌旁,撐著孩子的胳膊好讓他站在自己的腿上,面沖著我們。她看了看弗蘭,又看了看我。這次她沒有臉紅。她在等著我們的評論。
「??!」弗蘭叫出了聲。
「怎麼了?」奧拉立刻問。
「沒事!」弗蘭說,「我覺得我看見窗戶上有什麼東西,像是蝙蝠?!?/div>
「我們這兒沒有蝙蝠。」奧拉說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蘭說,「總之是有個什麼東西,算了,不說那個了。嗯,這小孩兒多好啊!」
巴德看著孩子,又看了看弗蘭。他向後翹起椅子,不住點頭,說:「沒事,不用擔心。我們知道他現在還贏不了什麼選美比賽。他不是克拉克?蓋博。不過給他點兒時間。要是他有運氣,說不定他能長得像他老爸一樣。」
(女人被眼前醜陋的孩子嚇到了,失態地叫了出聲,是失望還是悲傷?她期待看到的可愛天使竟然有著妖怪的長相。而巴德也看了出來,淡淡為了他開脫。)
嬰兒站在奧拉的腿上,看著坐在桌子旁邊的我們。奧拉把手向下挪點兒,抱住他的腰,好讓他能自己站著,肉乎乎的腿前後顫悠。毫無疑問,這是我看過的最難看的嬰兒。他長得是那樣的醜陋,讓我無言以對,嘴裡一個字也擠不出來。我不是說他病了或是有外貌上有什麼殘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純粹的難看。大紅臉,鼓眼泡,大賁兒頭,還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梢哉f根本沒脖子,長了三四個肥下巴,從耳朵下面就開始滾下來,更別提那對從光禿禿的腦袋上齜出來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噹啷著,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說他難看都是說輕了。
(男人把它說的毫無可取之處,彷彿是經驗裡所有的醜惡都在嬰兒身上匯聚,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女人也是如此,兩人沉默的看著另一對夫妻醜怪的感情結晶,在這之前,他們還一再給兩人展示一個理想家庭的模式,結果這樣的家庭,卻生出了一個不忍直視的醜怪嬰兒。理想的家庭圖景,難道會因為一個醜孩子而被打破嗎?)
這個難看的嬰兒發出奇怪的聲音,在他媽媽的腿上又蹦又跳。後來他不跳了,向前斜著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夠桌子上的碟子。
我見過不少嬰兒,我長大的時候,我的兩個姐姐加一塊兒有6個小孩,所以我小的時候老有嬰兒在我的周圍轉。在商店之類的地方,我也見過不少嬰兒。不過我以前見過的所有的小孩裡面,還都沒有能趕得上這孩子的,實在是太醜了。弗蘭也凝視著他。我猜她這時候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他的個頭夠大的,是不是?」我說。
巴德說:「過不了多久他就壯得能踢橄欖球了。在這個房子裡,可絕少不了他吃的。」
好像為了證明巴德說的話,奧拉用叉子插了些甜土豆,遞到嬰兒的嘴邊?!杆俏业男氊?,是不是?」她對這個肥肥胖胖的傢伙說,好像忘了我們的存在。
(奧拉與巴德自然的迴護他們的孩子,巴德若有所憾的找補,奧拉則是忽視其他人,試圖只建立母與子的關係,摒棄所有關係。
看到母與子的相處後,女人終於可以說出對孩子的稱讚。)
嬰兒向前傾著身子,沖著甜土豆張開了嘴。奧拉把叉子送進入孩子嘴裡的時候,孩子一口咬住了叉子,嘴裡嚼著,在奧拉腿上不住地搖晃起來。他的眼睛是那樣的凸起,像插頭一樣塞在什麼東西裡。
弗蘭對奧拉說:「這孩子真不錯?!?/div>
嬰兒的臉皺成一團,又開始折騰起來。
「讓喬伊進來吧?!箠W拉對巴德說。
(被關在外面的孔雀,因為嬰兒吵鬧的關係得以進到屋裡。故事的核心,和故事的謎,兩者終於要碰頭了。)
巴德讓椅子翹起的腿又重新著了地,說道:「我想咱們至少應該先問問人家是否介意?!?/d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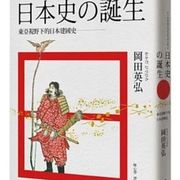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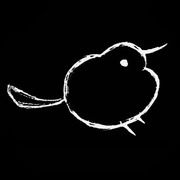


 達人 讀後心得|《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村上春樹
達人 讀後心得|《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村上春樹
 4
4
 1405
1405









奧拉看了看弗蘭,又看著我。她的臉又變紅了。嬰兒還在她腿上興奮地騰挪跳躍,使著勁想要下來。
「我們都是朋友,」我說,「你們想怎麼著就怎麼著吧」。
巴德對奧拉說:「說不定人家不想讓屋子裡面有只像喬伊那樣的老鳥,這點你想到過嗎?」
「你們介意嗎?」奧拉問我們,「如果讓喬伊進來?那只鳥今天晚上真是有點兒反常。這孩子也一樣。不過這孩子可能是習慣睡前讓喬伊進來,和他鬧騰鬧騰。今晚他們兩個看來都不會消停了?!?/div>
(此時孔雀的作用就和一般的寵物一樣,同時也是奧拉用來化解,或者說是揭露醜陋嬰兒真相的關鍵手段。)
「別問我們了,」弗蘭說,「讓它進來我沒意見。我還從沒和孔雀離得那麼近過呢。不過,我不介意?!顾戳丝次遥蚁胨且乙脖硎颈硎?。
「當然沒事!」我說,「讓它進來?!刮夷闷鸨樱豢诤裙饬伺D?。
(說完話後把眼前的飲料一飲而盡,有沒有一種把剩下的話跟著飲料吞下肚子的感覺?男人到底吞下的話是甚麼?他不想要孔雀進來嗎?為甚麼不想要?巴德是否也不想要?是不是只有女人們期待看見孔雀出現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巴德站起來,走過去,打開了前門,又把門廊裡的燈打開了。
「你孩子叫什麼名字?」弗蘭想知道。
「海拉德?!箠W拉回答。她又從自己盤子裡拿了些甜土豆給海拉德吃。「他很聰明,小猴子似的那樣機敏。你說什麼他都明白。是不是,海拉德?等你們有了自己的孩子,弗蘭,你就知道了」。
(「等你有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了?!?/font>
女人在思考著甚麼,不知不覺中,這個房間的重心從剛開始兩朋友與妻子的應對,逐漸轉移到母與子的關係上面。巴德和男人,原先邀約得以成立的關鍵人物,現在屈居於展示的背景布。就像是一個家庭的變化,由兩人世界逐漸演變成父母兒女後,男人在當中不可避免又成為多餘的存在,巴德已經淡然接受了,而男人還未必。)
弗蘭只是看著她,沒說話。我聽見前門開了又關了。
「他是挺聰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又回到廚房說,「隨奧拉她爸?!?/div>
在巴德的身後,我能夠看見那只孔雀正在客廳裡轉悠,左右來回扭著頭,就像你轉動手裡的鏡子,它要左右搖頭才能看清楚自己。它不停地抖動著自己的羽毛,聲音讓人覺得就像是在別的屋裡有人洗牌。
(像是有人在洗牌一樣的聲音,這是多貼切日常的比喻,既涵蓋牠玩耍的動作與聲響,也有著孔雀入局,大家重新整理認識現在場景的意思。)
它向前邁了一步,然後,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嗎?」弗蘭對坐在桌子對面的奧拉說,說話的樣子就像是如果奧拉允許她抱的話,就是幫了她一個忙似的。
(奧拉的情緒變化,有點像是希望藉由抱孩子,彌補之前的失禮,迎來了對孩子印象的轉機。)
奧拉把小孩遞給弗蘭。
弗蘭試著讓小孩老老實實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孩子老是扭動著身子,發出各種聲音。
「海拉德!」弗蘭叫著。
奧拉看著弗蘭和小孩,說道:「海拉德的爺爺16歲的時候,開始讀百科全書,從A到Z,他還真讀完了,就在他20歲的時候,他碰上我媽媽前不久。」
「老爺子他現在在哪兒?」我問,「他是做什麼的?」我想知道一個曾經定下那樣目標的人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死了。」奧拉回答我說,但目光仍在弗蘭身上。弗蘭已經讓小孩仰面躺在自己的膝蓋上了。她輕輕逗弄著小孩的下巴,並開始模仿兒語和他說話。
「他以前是伐木的,」巴德說,「別人砍的樹砸在了他身上」。
「保險公司賠了媽媽些錢?!箠W拉說,「但她都花光了?,F在是巴德每個月給她寄些錢?!?/div>
「也不多?!拱偷抡f,「我們自己也沒什麼錢。誰讓她是奧拉她媽呢?」
(為甚麼引出了爺爺立志的故事?又為甚麼這個故事結束在一個毫無所謂的死亡上面?這中間的空白到底是甚麼?在他們逗弄孩子的時候,草率地談論老人面目不清的死亡。那些空白的日子,在新生的孩子中被不合時宜的想起,又隨意的扔棄,回到那個寡婦一文不值的現實。
一閃即逝的訴說,生命即便由一個壯志開始,而壯志也能得酬,卻也被大段空白所覆蓋,最終停格在一個沒有意義的死亡。
在講述展現一個理想家庭的時候,作者卻選擇插入一則死亡事故,曖昧的表示著,眼前所謂的家庭生活,也不過是臨時寄託的價值,死亡與空無並不會因此繞道而行。)
到這個時候,孔雀已經攢夠了勇氣,開始在一種搖擺顛簸的運動中,從客廳向餐廳這邊慢慢靠過來。它頭挺到一定的角度,用紅眼睛盯著我們。頭頂上的枝狀羽冠有幾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葉伸展開了。這傢伙在離桌子幾英尺的地方停了下來,審視著我們。
(天堂鳥,巴德的感嘆,當孔雀開屏的時候,即便曾經嫌棄它骯髒的人也不得不被那樣子所眩惑,孔雀總是帶著審視的眼神觀看眾人,牠在評價甚麼?
此時孩子對女人的吸引力已經遠遠超過天堂鳥。)
「他們叫它天堂鳥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拱偷抡f。
弗蘭沒有抬頭看,她全部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她開始和小孩玩拍手遊戲,嬰兒好像挺喜歡。這傢伙不再鬧騰了。她把他抱起來,輕輕地和他耳語。
「好,」她說,「不許告訴任何人我剛才說的話啊?!?/div>
(女人和孩子之間的悄悄話,她究竟說了甚麼?這是整個故事中無從解答的謎題,也是一個還算甜蜜,答案無所謂的謎題。)
小孩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視著她,然後伸手抓住了一把弗蘭的金髮。孔雀又向著桌子靠近了一點。大家誰都沒說話。我們只是平靜地坐著。嬰兒海拉德看見鳥,鬆開了弗蘭的頭髮,在她大腿上站了起來,跳上跳下,用自己的胖手指指著鳥,嘴裡發出各種聲音。
孔雀快速地繞著桌子跑向小孩,它的長脖子伸到小孩的腿之間,嘴巴鑽進小孩的睡衣裡,僵硬的腦袋前後顫動。小孩笑著小腳亂踹,靠背部的移動,費力但迅速地從弗蘭的膝蓋滑到了地上??兹竿妻⒆?,好像在和孩子玩什麼遊戲。弗蘭把小孩拉回到自己的腿邊,孩子卻使勁地掙脫,還想向孔雀爬去。
「我簡直不能相信?!垢ヌm說。
「這只孔雀瘋了,就是這麼回事!」巴德說,「該死的鳥不知道自己只是一隻鳥,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奧拉咧著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齒。她看著巴德。巴德沖她點點頭,把自己的椅子從桌子邊拉開。
這真的是個難看的小孩。但,就我所知,這對巴德奧拉來說無關緊要。即使和他們有關係,他們可能也只是想,好,孩子是難看點兒,怎麼了?他還是我們的寶貝。當然,現在孩子還小,這只是一個階段。不久,就會有另一個階段。有這個階段,還會有下一個階段。等所有的階段都經歷過後,最後就會沒問題了。他們說不定就是這樣想的。
(男人在洞悉了人們看待悲哀事情的盲目樂觀本質,這個階段的醜陋與問題,到了下個階段就不一定如此,這些階段都有其意義,在於彰顯前面的階段被經歷過後,當所有階段都結束後,原來的問題還在嗎?可能不在了,畢竟到最終,甚麼都會消失,連問題也是。
男人似乎找到了能解決問題的無限方法,只要相信下個階段會帶來變化,他又可以沉入編織的承諾神話故事裏頭,相信生活的問題會在將來被解決。這樣浮士德式螺旋上升的敘事,構成了現代生活的基底。生活是充滿著空白無意義的噪音與雜訊,然而我們卻可以說服自己,生活不過是個階段,為了達到某種更好境界的過程,所以我們能夠忍受這樣的生活,忍受所有,在忍受的同時,又矛盾的質問自己,為了一個不明意義的終點,這一切值得嗎?)
巴德接過孩子,把他蕩過自己的頭頂,直到小孩尖叫起來??兹肛Q起羽毛,注視著一切。
弗蘭又搖了搖頭,衣服上有嬰兒剛才弄皺的地方,她把它重新展平。奧拉拿起叉子,吃著盤子裡的青豆。
巴德把小孩轉移到自己的胯部,沖我們說:「還有餡餅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奧拉家的那晚很特別,我知道那是特殊的一晚。那天晚上,我幾乎為自己生命裡擁有的一切都感到高興。我真的等不及想和弗蘭單獨待在一起,好早告訴她我的感受。那晚,我又許了個願。坐在桌子旁,我閉上眼,使勁地想。我許的願是我能永遠不忘了那個晚上。在我的願望裡,這一點是實現了的。對我來說,這個願望的實現是我的不幸。不過那時我當然不會明白到這點。
(不忘記這夜晚的不幸是甚麼?這中間發生甚麼事情?空白,裡面的空白就是不幸的源頭,那些空白不是真正的空白,而是如開頭所言的,猶如發生在別人身上的空白。在那些空白之外,牢牢記住的是這個令他重拾信念的一晚,理解到那晚熱情的背後,是更深層的絕望。)
「你在想什麼呢,傑克?」巴德問我。
「隨便亂想?!刮艺f著,沖巴德笑了笑。
「發呆呢?」奧拉說。
我只是又笑了笑,搖了搖頭。
那晚,從巴德和奧拉那兒回到家,躺在被窩裡,弗蘭說:「親愛的,用你的種子填滿我吧!」她說這話時,我全身都聽到了,從頭到腳,我大叫著釋放出來。
後來,當我們的情況變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蘭總會想起在巴德家的那個晚上,覺得那是一切改變的開始。但她錯了。改變是在那之後來的──而當改變真正出現的時候,那改變卻好像是發生在別人的身上,而不是什麼可能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似的。
(即便在那天,他們都還相信任何改變都在他們願望與掌握之中,他們對生活依然抱有熱情。
而男人從未來發聲,殘酷的打破這個幻想,真正的改變是一種疏遠而冷漠的感覺,與那晚溫馨熱情截然不同。)
「操,那些人,還有那個難看的小孩!」有時我們深夜看電視的時候,無緣無故地,弗蘭就會突然這樣說。「還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基督耶穌啊,要它做什麼啊?」雖然自那次以後她再也沒見過巴德和奧拉,她還是經常說一堆這樣的話。
弗蘭現在已經不在奶品廠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頭髮。她長胖了。不過我們不談這個問題。有什麼可說的呢?
我倒是還會在單位裡看見巴德。我們一起工作,一起打開我們午飯的飯盒。如果我問起,他會和我聊奧拉和海拉德。喬伊的情況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飛進了巴德院裡的那些樹裡,就不見了,再沒有下來。老死了吧,巴德說。後來那些樹被貓頭鷹接管了。巴德聳了聳肩。他邊吃三明治邊對我說,將來有一天海拉德會成為一名橄欖球後衛?!改阏鎽撊タ纯茨呛⒆?。」巴德說。我點點頭。我們還是朋友,這一點一直都沒變。不過我和他說話時變得小心了起來。我知道他感覺得出來,他希望不是這樣。其實,我也希望不是這樣。
只有很偶然的時候,他才會問起我的家庭。當他問起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大家都挺好?!复蠹叶己?!」我說。我會合上飯盒,掏出香煙。巴德會點點頭,抿幾口咖啡。
(在那天,看似溫婉體貼的女人,彷彿已經全盤接受巴德夫婦,並且似乎與他們結為好友的弗蘭,最終對那天的一切變得挑剔刻薄,並且耿耿於懷,中間究竟發生了甚麼?空白,一段漫長到可被忽略的空白。
在這空白後,他們變得不再談論長髮的事情,不再談論吸引和情感。
天堂鳥也在一片空白中消失於樹林裏頭,老死了,巴德夫婦習慣有牠作伴,然而牠卻在有一天,毫無預兆的轉身離去。那天堂鳥究竟是甚麼?為甚麼夾在一串失落的感情之間被提起牠的消失?)
事實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種喜歡拐彎抹角欺騙的天性。但我不說這個。甚至和孩子他媽我都不談論這些,連提都不能提。我們之間的談話越來越少了。談的話也幾乎都是關於電視。但我還記得那晚。我回想起那只孔雀邁開灰色的爪子,繞著桌子緩慢移動的樣子。還有我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門廊上和我們說再見的情景。奧拉送給弗蘭幾根孔雀的羽毛帶回家。我記得我們都握著手,擁抱著對方,說這說那。在車裡,回家的路上,弗蘭緊貼著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們就這樣一路從我朋友巴德那兒開回了家。
(在不是現實中的最後一刻,在記憶當中的結局,是一個很美,很柔,彷彿能成為永恆情誼象徵的一幅圖畫。這或許才是生活真正的痕跡,不是長髮、牙齒矯正、孔雀或者孩子,而只是一段專屬於個人,無法分享給伴侶或任何人的記憶斷片。)
作者相關創作
相關創作
[閱讀筆記] 日本史的誕生 - EP.3
 8
8
 73
73
[閱讀筆記] 日本史的誕生 - EP.2
 6
6
 78
78
[閱讀筆記] 日本史的誕生 - EP.1
 4
4
 80
80
【閱讀】獸靈之詩:我想我是真的不懂詩
 3
3
 401
401
[閱讀心得]全球銀力時代
 0
0
 455
455
閱讀筆記|分享一下近來的讀書概況-20220929
 11
11
 377
377
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
 10
10
 860
860
《學生會偵探桐香》第一卷心得
 3
3
 30
30
日影
 6
6
 37
37
《龍王的工作》第十八卷心得
 4
4
 28
28
57冊
 6
6
 33
33
《透過機器人與你相戀》心得
 3
3
 40
40
【小說研究相關】關於小說的開頭.
 10
10
 92
92
逐步修正
 4
4
 59
59
《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心得
 3
3
 125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