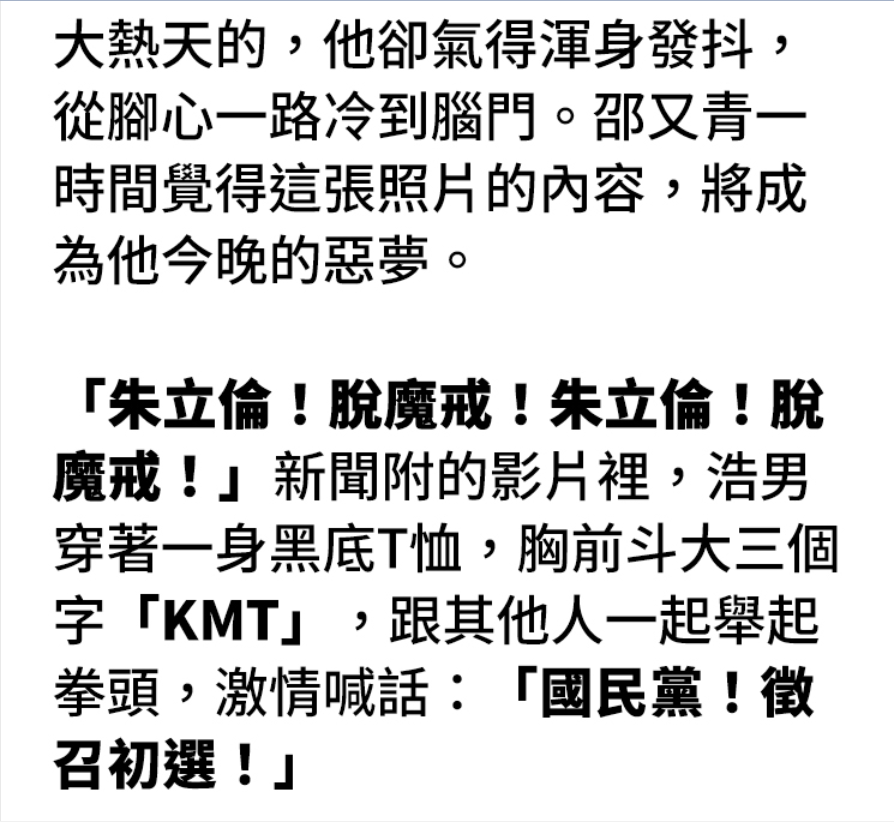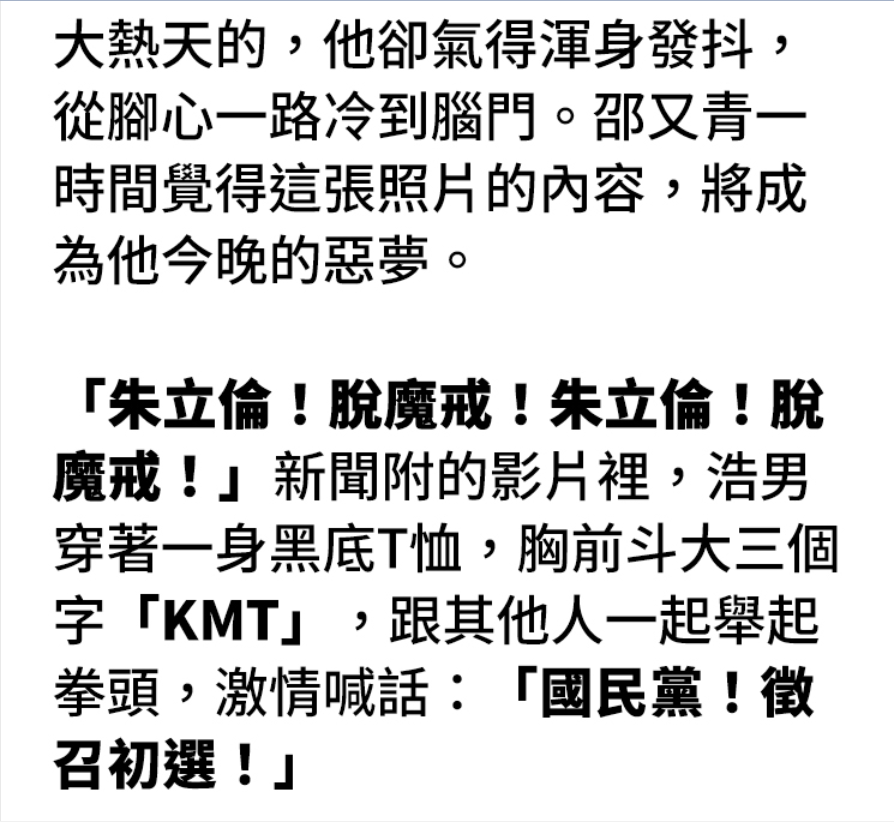因?yàn)轫n粉這篇真的很樂所以要多放 (X)
※今年寫作:
一月~三月:《謝新恩》(完)
四月:《古代美人把我養(yǎng)成替身》(完)
五月:《韓粉》(完)
六月:《非典型追妻火葬場》(完)
七月~十月:《五體不滿足》(修稿中,未完)
十一月:《德爾斐的憂患之子》(完)
十二月:《歐西里斯的祝福》(連載中)
一月:
(七)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謝新恩之宮闈秘談》)
李從嘉等著大癒,還須調(diào)養(yǎng);趙元朗卻不再像上一回他發(fā)燒時(shí)那麼關(guān)心。許是有些政務(wù)要忙,一連幾日,玉英閣特別冷清。
別的人怕鬧病了,不得聖駕;李從嘉反望著這病鬧得久些,免得趙元朗來攪擾他一個人過活。
沒了周嘉敏的看顧以後,李從嘉或是看書,或是寫字,都懶懶的,只是懨。他想:「倒好,當(dāng)初既是被擄來這兒伺候他,如今就這麼孤家寡人、乾乾淨(jìng)淨(jìng)地伺候他一輩子。」
七夕雖剛過,午後卻依然悶熱。閣外金磚被毒辣辣的日頭照得生煙,雖有小廝在外頭給竹子灑水,還是涼意全無,一絲風(fēng)都沒有。
在趙元朗的吩咐下,玉英閣宮門深鎖,竹簾低垂;仍是那被幽閉、軟禁時(shí)的模樣。李從嘉更覺七夕那日難得可以出宮,已是天子莫大的眷顧;也令他已什麼都不敢想望、奢求。
外頭澆水那小廝打開簾子,進(jìn)屋了,「侯爺,奴才接了信,待會兒唐太醫(yī)還要過來問脈。現(xiàn)在暑意甚濃,侯爺不妨歇歇,否則脈象浮了,太醫(yī)也看不準(zhǔn),皇上還得操心呢。」
李從嘉笑道:「皇上只會為國事操心,哪裡有為我操心的份?」小廝也不搭理侯爺話裡的刻薄,兀自來更換房裡已經(jīng)融了的冰雕,期間說幾句閒話。
待小廝將青絲細(xì)竹涼蓆鋪設(shè)好,李從嘉躺上去斜倚著,素紗的衣裳已被濡得汗津津的。便說:「墨池,幫我換件衣服吧,這件濕了。」
那小廝原是叫墨池的,回過話說:「侯爺,其餘幾件都拿去洗了,只餘一件,奴才本是想留待聖駕。」李從嘉擺擺手,「哪來這許多美事,別整天想望這些。」
墨池說:「皇上冷落也只是一時(shí),侯爺何必自棄呢?」李從嘉沒回他,墨池只好去揀了藕色的出來,讓李從嘉換上,又為他搧風(fēng),服侍著他睡下。
李從嘉面壁裡睡著,半晌覺得搧起的風(fēng)大了好多,快意得很,迷迷糊糊地說:「這風(fēng)搧得很是舒服,否則暑悶難忍。」
那邊搧風(fēng)的人輕聲道:「好。」又笑道:「臣以為南方更熱,侯爺比較耐暑,想來也是怕熱,恐怕這幾日夜裡不好睡下。」話語很是溫文。
李從嘉聽著這人並非墨池,那人又替他把涼被掩上,「出這麼多汗還吹風(fēng),侯爺現(xiàn)在體虛,易受風(fēng)寒,還是仔細(xì)掩著罷。」他也懶得起來,又睡了一陣子,那人也沒走,只是替他搧風(fēng)。
過了半個時(shí)辰,墨池進(jìn)來,「唐太醫(yī),真對不住,這玉英閣裡左右只有我一個奴才服侍,主子過去又是個天家的命,特別嬌貴,害得您耽擱在這兒,哪裡都不能去。」
唐識幾搖搖頭,很是客氣地說:「也多虧李侯爺,過去我總是得進(jìn)六院裡替娘娘們問平安脈,現(xiàn)在倒好,免了這慣例,只需盡心將李侯爺?shù)纳碜诱{(diào)養(yǎng)到好。若只是照顧李侯爺一個,我也省心不少。」
墨池打趣笑道:「唐太醫(yī)也是喜歡李侯爺?shù)膯幔坎蝗缜罅嘶噬希嫔线€是宮裡的御醫(yī),只是住到玉英閣裡,早晚查看也不至於出亂子。」唐識幾不敢唐突回話。
倒是李從嘉醒了,輾轉(zhuǎn)反側(cè)間衣帶半褪,精緻的鎖骨與白白的胸脯微露,一副美人春睡的曖昧情味兒。唐識幾看了一晌,喉頭發(fā)乾,臉上微紅。
墨池心知李從嘉是皇上的人,趕忙替他披衣,不好讓這肌膚被別的男子看去。
李從嘉只當(dāng)墨池是怕他著涼,沒多在意。道:「我這閣子裡太過清靜,確實(shí)無趣,但唐先生好歹食著宮中俸祿,與其讓他來照顧我這廢臣,還是往後宮裡替娘娘們看脈比較容易發(fā)達(dá)。」
又說:「其實(shí)也沒什麼脈好望,不是都大好了?」
唐識幾見得李從嘉消瘦清減,未免憐惜,情切道:「方才臣捏了一下,病色絲毫未減。若是能將往日裡的病根子一同盡除了,臣才放心。」
李從嘉並不如何,「我無處可去,禁錮之身,鎮(zhèn)日只是坐在這兒,看天光東起西墜,無聲流轉(zhuǎn)。病得再深,終有一日會好的,也不需如此煩擾太醫(yī)。」
又說:「你若覺著這差事無趣,我請墨池去向四喜公公說了,你也不必再進(jìn)玉英閣。」
唐識幾忙說:「宮裡侍奉很是勞碌,還是這兒清閒些。」不願李從嘉攆他走。
「與其回御藥房裡替那些金貴的娘娘們開方子,猶恐出了什麼差池,侯爺是個知情識趣的主兒,在這兒打扇子也還好些。」
李從嘉聽這話,倒有點(diǎn)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味道了,平平都是來侍奉趙元朗的,就沒再說話攆他。
儘管身無長物,還是吩咐墨池,「近日裡畫的幾張畫,你從裡頭揀一張好的出來。」墨池找了張臨竹子的,交給唐識幾。
展開一看,是一卷墨竹,濃淡相間,風(fēng)神綽約。見到是李從嘉親手的字畫,雖說能市百金,可畢竟是宮中之物,唐識幾一時(shí)間還不敢收。
李從嘉見他生份,微微一嘆,「我的父親、兄弟、妻子都已離我而去,子美曾說『冠蓋滿京華,斯人獨(dú)憔悴』,我雖不是太白,倒也沒半個能說話的人了。唐太醫(yī)這可是在絕我的念想,果真還是回過聖上,讓你不必來的好。」
聽他娓娓道來,那人無意間的眼波流轉(zhuǎn),莫名牽動唐識幾的心緒,又想起他方咬舌自絕那時(shí),皇上坐在他的床畔,對他是如何地要緊,更覺李從嘉可人之處,他算是明白為何皇上非得在宮中偷偷養(yǎng)著這個人了。
便將那張畫捲起,收入囊中,不禁握住那隻纖長白皙的玉手,「皇上的福氣,臣是羨慕的。」
李從嘉也未察覺這名小太醫(yī)在對他說些渾話,只尋常道:「你未作過天子,怎麼知道作天子的人有哪些福氣?」
唐識幾望著李從嘉那俊秀嬌豔的面龐,幾不可聞地說:「不說能擁有半壁江山,單是能擁有侯爺您……已是不可盡言的至福。」
那廂聲音卻道:「怎麼?朕的人,你一個小小太醫(yī)也動心了?」原是趙元朗除了龍袍,已換上宮中尋常衣裳,擺駕過來了。他故意不要四喜通傳,想在傳晚膳前過來看看,沒想看到眼前這畫面。
趙元朗鳳目一瞇,眼神已變得危險(xiǎn),眼裡的光很是灼人。
唐識幾見狀,猛然跪下,「陛下恕罪!」
李從嘉倒沒怎麼,不行禮也不求饒,還是那樣懨懨地歪在榻上,冷冷地勾了勾唇角,「派人來捏脈的是皇上,脈真的捏了,反而是捏脈的人多事。皇上若是要臣死,就不必派人來捏脈,讓臣在這兒自個兒慢慢死了便是,也不至於驚擾別人。」
趙元朗心知李從嘉說的也在理,只是又不理解,究竟是唐識幾色膽包天,還是李從嘉狐媚勾引,怎麼幾日未過來,就成這副德行了。
當(dāng)下也不好處置唐識幾,只冷聲道:「你下去,以後不許再來。」得了大赦,唐識幾不敢忤逆,謝恩而去。四喜很是識相,讓墨池去煮茶,自個兒退出去了。
趙元朗來床側(cè)坐著,「朕讓四喜從膳房裡端了些冰碗來讓你解暑。」話裡很是體貼。又想抱李從嘉,那人只是躲閃。
李從嘉道:「不也是那些娘娘侍妾們吃剩不要的,才有輪到臣的份?臣本不比她們嬌貴,又何須解暑?」
趙元朗心知是自己這幾日來懶怠,疏於走動,冷落了李從嘉,他又與自己生了嫌隙,心結(jié)始種,就不好解。
也沒生氣,只捏捏李從嘉清減的下頷,「給你的自是不從別人那裡拿,這是朕自個兒內(nèi)膳房裡取的。朕的份例就是你的份例。」
「是那些人比不過你,不是你比不過她們。」
見趙元朗在討?zhàn)垼顝募螞]作聲。
皇上又說:「那個小太醫(yī)倒是有些能為,朕幾日沒來,你臉色已紅潤許多了。」
李從嘉怕趙元朗殺了唐識幾,便有意無意地說:「今日診察時(shí),是說先前的病根子落了灶,表面上好了,病氣還在。」
趙元朗道:「上次那個替你看病的不好麼?」
李從嘉說:「病根子都落了灶,還行吧。」
趙元朗不願李從嘉繼續(xù)同他置氣,只好服了軟,「若唐識幾的醫(yī)術(shù)確實(shí)不錯,讓他繼續(xù)顧著也是可以,只是朕再多讓人看著。」
「從嘉,你是這般國色天香,尋常男子見了你也動心,朕不怪他。你若不如此出挑,朕也不會這樣慣著你。」
身為一名男子,還要被說是國色天香,李從嘉才在冷笑,一時(shí)間,四喜敲了門。
李從嘉起來坐了坐,整理了衣裳。四喜進(jìn)來道:「陛下,晚膳時(shí)分已至,皇后娘娘通傳,請陛下擺駕過去,一塊兒用膳呢。」
趙元朗看了李從嘉一眼,李從嘉道:「臣這玉英閣裡,也沒甚麼東膳房、西膳房、外膳房、內(nèi)膳房的。既然皇后娘娘思君甚苦,臣也不好強(qiáng)留皇上,沒的敗壞朝綱。論起品級,皇后娘娘著實(shí)還在微臣之上呢。」
皇上一嘆,「若是能,就是要廢后,朕都想讓你作個皇后。」
李從嘉涼涼地說:「臣躬德薄,陛下隆恩過熾,臣無福消受。」
趙元朗拿他也沒輒,只對四喜擺了手,「告訴皇后,朕今晚不去她那兒。」
四喜點(diǎn)了頭,又提醒道:「陛下,這個月,『九九而御』天數(shù)尚未滿呢。」原是趙元朗陪著李從嘉的時(shí)間長,如今已是八月下旬,後宮尚未雨露均霑。
李從嘉看都不看趙元朗,擺頭向壁裡,只說:「微臣也不能給皇上誕下個龍種,萬望皇上以國事為體,快請移駕吧。」
趙元朗見他那倔強(qiáng)樣子,以為他在喝醋,捏著他的手,一隻手來回摸著他的大腿,向四喜說:「你下去吧。」四喜回了聲「遵旨」,便不再進(jìn)來。
皇上今晚便留宿了玉英閣,餘下諸事暫且不提。
二月:(謝新恩)
(二十六)兄友弟恭
宮外仍在小雪,入夜了,冷風(fēng)颳得一陣陣,書房裡點(diǎn)著紅燭。為了替趙元朗祛寒,炭爐裡燒不少炭火,覷得屋裡頭很暖和。香獸鏤格中溢出的蘭香在暖室中繚繞得氤氤氳氳。
這幾日來趙元朗都睡不著覺,明日一早,就是李從嘉頭七,抑是停靈的最後一日。
龍床上,趙炅自後頭摟著他,牽動鎖鏈發(fā)出聲響,「怎麼?今晚也睡不著?」
趙元朗想到弟弟白天還得上朝,是自己吵醒他,不由說句:「光義,對不住。」
……還是叫他光義。在那人的眼裡,自己永遠(yuǎn)都是光義。
他說:「大哥,李從嘉已經(jīng)死了。」把手捂在趙元朗的小褲上,握著情根上下捋捋,含著趙元朗的耳垂,吐著熱息,「你也該忘了他,不然你難道以後每晚都不睡覺了?」
怎麼忘了那個人?倘若那麼簡單就能忘記,又何必惦記著他十年不來汴京朝覲之事;又怎會自大半輩子前金陵一見伊始,就始終掛心?
趙炅半挺的情根抵在趙元朗緊緻的臀縫間,隔著小衣蹭了蹭,深怕牽動他琵琶骨的傷,把人弄死在床上,不敢太大力。
手握著趙元朗那無一絲贅肉的腰肢,來回摸了摸。趙元朗本因著功體被摧,總是溫涼的身體,竟因著這曖昧的觸碰而陣陣發(fā)熱。
那人沒反抗──當(dāng)然也沒辦法反抗,就是翻個身都困難。
趙炅將趙元朗翻過身來面對自己,見他緊張得喉結(jié)上下一動,吞了口口水。親上他的眉骨,鼻尖,直到唇瓣,趙元朗將兩片薄唇抿得死緊,忍著痛別過臉。
「大哥,你究竟要到何時(shí),才肯接受朕?」
趙炅動作極慢,拉開趙元朗的小衣,露出赤裸而清減的胸膛。趙元朗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今已是深夜,無事不會再有任何內(nèi)侍進(jìn)門打斷。四肢皆是綿軟不可出力,帝王的臨幸竟是避無可避。
皇帝把臉埋在趙元朗的脖頸間細(xì)細(xì)廝吻,一隻手捂弄在他形狀仍然飽滿的胸膛上,「大哥,朕讓你累一點(diǎn),一會兒你自然就睡著了。」可是從今以後,他又該如何看待光義呢?趙元朗不明白。
趙炅低頭吮吻大哥的胸,一下就把這對蜜色的奶子吻得佈滿青紫瘀痕。虎牙方在乳暈上咬下,趙元朗「唔」的一聲,渾身一顫,臉上已帶著紅暈。
鮮紅的牙印清晰,大哥的身體頗為敏感,可面上依稀還有些不情願,趙炅玩賞般看著,笑意裡帶點(diǎn)玩味,「對你而言,朕還是光義,是你的弟弟;可是大哥,你已經(jīng)是朕的奴隸了,別忘了這點(diǎn)。」
一晌,撕心裂肺的痛自下體間擠入,趙炅分開他的大腿,撕破他的小褲,掰開臀縫,將已然梆硬的巨物插進(jìn)仍然緊澀的小穴中,壓在大哥的身上,沉沉地喘著氣,額角沁出幾點(diǎn)冷汗。
『沒有東西可潤滑,想來光義也是難受。』趙元朗綿軟無力的手摁著皇帝的肩膀,緊蹙著眉,忍受那人銳利的兇器破開他青澀的處子之身,無情挺入。
飽脹的陽根在他緊澀的體內(nèi)突突地跳著,趙元朗因著疼痛已面色發(fā)白,顫抖著吻了吻趙炅的臉頰,「光義…、」難受得洩出一絲輕吟,「…哼嗯……」
趙炅見大哥對他的態(tài)度似是有所改變,不覺間浮了腰,停了半晌,不再那麼用力地貫穿他、要他的命,而是淺淺地用已覆上薄薄血色的龍根,在入口的皺摺處淺挖著,「乖就好,大哥,朕輕一點(diǎn)弄你,等會兒射你裡面,給你播龍種。」
給他這男人播龍種,有什麼用呢?這話聽來很好笑,可是趙元朗笑不出來。皇帝是認(rèn)真的。
趙元朗已試圖努力放鬆全身;藉著血的潤滑,趙炅也掏挖得順?biāo)煨辉俑械金姥e那麼乾澀;分明是一具不適合被進(jìn)入、擁抱的身體,偏生趙炅要的是他。
──光義他是辛苦的,我們各自都有難處。
趙炅摁著趙元朗窄緊的腰肢,一下、一下地狠操著他的大哥。趙元朗疼得頰色脹紅,表情扭曲,但是一聲不吭,牙關(guān)咬得太緊,一絲血自他嘴角滑落,被趙炅伏首舔去。
「大哥,在朕的身子底下叫出來又有何妨?叫啊。」似是要逼出那人的嬌喘,粗長肉棒的侵入很是張狂。儘管疼痛,然而花徑中畢竟敏感纖細(xì),隨著碩大的龜頭來回刮擦過緻密的穴肉,帶來極致快意,趙元朗終究還是忍俊不住,低沉地洩出幾聲喘息,「哼嗯…、…呼……」
「大哥以後就是朕的女人,能承朕的雨露。堪為大宋表率!」
趙元朗的順服令皇帝龍心大悅,他一下、一下地送腰。一記深頂,堅(jiān)硬的龜頭竟直直頂?shù)浇Y(jié)腸口,插進(jìn)結(jié)腸。
「哈啊──…!」霎時(shí)間,趙元朗眼白一翻,渾身一個激靈,這表情被皇帝看得清清楚楚。
大哥居然爽到翻白眼,就算他和李從嘉曾做過無數(shù)次又如何?李從嘉難道能讓他翻白眼麼?趙炅見狀很是得意。果然,贏的人還是自己這作皇帝的。
說什麼都必須向大哥證明自己的皇威、自己已是主宰他的那個人,規(guī)矩必須立下。君臨天下的人不是別人,只能是他。
趙元朗已不能行走,雙腿雙腳只能綿軟地?fù)卧诖裁嫔稀Zw炅將一條腿抱在自己腰側(cè)。和趙元朗比起來,皇帝的臂膀是那麼地有力。
明明是強(qiáng)迫受辱,但趙元朗腦子一熱,竟感覺前面有些癢。他恨不得摳兩下自己的鈴口解癢,可是被穿琵琶骨以後,他手不能舉,強(qiáng)烈的快感還在刺激著他,沙啞的嗓音中已帶些欲泣的情緒,「光義……哈……幫大哥摸……」
那個向來高高在上、視他如無物的大哥,竟然會為了區(qū)區(qū)性欲,這樣可憐巴巴兒地哀求他!也終於到了這個時(shí)候。
趙炅笑道:「大哥既然已經(jīng)是朕的女人,怎麼可以用雞巴射呢?」說完,用力地彈了已腫脹的紫紅色龜頭一下。
「唔…!」趙元朗疼得生理性的淚水都自眼角滲出,這一疼,卻是熾熱的綿軟肉穴劇烈抽搐,緊緊收縮,將趙炅夾得彷彿要斷氣,「大哥,你真的好緊,好會夾,操起來比誰都舒服……」往下一覷,只見鮮紅的媚肉夾雜著鮮血,將爬著青筋的粗大龍根盡數(shù)吞吃,很是淫靡。
「這樣的癡態(tài)便是太上皇咯。」趙炅冷笑著,滿意地打了趙元朗窄緊的小屁股,窄緊的肌肉發(fā)出彈手響聲。
不論光義如何屈辱他,趙元朗都接受,心知這都是自己欠他的。
幽密的後庭雖非情事之處,然皇帝操幹得厲害,那處既已破身,也愈發(fā)爛熟。趙炅得趣之際,竟不顧趙元朗的傷勢,用肩膀扛著他的大腿,大開大合地操幹起來。
「啊……!」晃動間,趙元朗鎖骨上被鐵勾刺穿的傷口,硬生撕裂開來。嫣紅的鮮血順著胸膛一路流淌至床面,浸濕黃錦羅緞成了暗紅色。
皇帝的腰胯不停拍打著趙元朗的臀口,發(fā)出「啪啪啪」的響聲。混著血腥味、精臭、蘭香,龍寢內(nèi)滿浸靡爛情慾。
每當(dāng)傷口勾動時(shí),趙元朗的面上便浮現(xiàn)一抹奇異的艷色,癡態(tài)看上去甚是冶豔。趙元朗不但不怕痛,痛甚至引逗他的情潮,令他更加孟浪。
大哥分明是一介偉岸男子,在龍床上委頓承歡的媚狀,卻使得趙炅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趙炅嘴角微微一勾,瞇起細(xì)長的一雙丹鳳眼,竟把住傷口已然迸開那側(cè)的鐵鉤,用力往開裂的血口子中攪拌晃動。
「──啊啊啊!哈啊!」翻弄的鐵鉤掀開皮膚,露出其下血淋淋的肌肉,幾絲肌腱已斷裂開來。鮮血泉湧般浸濕床面,趙元朗汗如雨下,兩隻眼睛往上一吊,不勝排奪之苦,竟?fàn)柮媛兑鶓B(tài)。
隨著趙炅頻頻操幹他已軟弱無力的小臀,至深力道頂入他委曲花心深處,「哈…、…」盡力壓抑著淺聲低吟,趙元朗竟夕出精,濃稠的瓊漿淋漓地射透自己的中衣與腹肌。
趙元朗高潮時(shí)那一夾,著實(shí)令人喪魂銷魄,哪個後宮嬪妃曾給過他這種九彩昇華齊聚頂?shù)淖涛秲海抠咳唬w炅被夾射,沉沉睪丸內(nèi)所有汁水一股腦全射進(jìn)哥哥體內(nèi)。
「哼嗯…、…唔……」眉心緊蹙,趙元朗猶感腸壁被用力噴射,下腹內(nèi)傳來一陣受精所帶來的鈍疼,直至皇帝喘息著抽出染血的龍棍。
龍根方出,淫靡的白漿混雜著血液,自太上皇的雙腿間汩汩流淌出來;趙元朗早已四肢百骸都?xì)埰啤喩硎茄瑓s還支持著意識,尚未昏厥,迷離的眼神瞅著在他身上揮汗如雨、顛鸞倒鳳得不知天地為何物的親弟弟。
閣內(nèi)血腥氣甚重,甚至蓋過龍精的氣味。
那傷口若不即時(shí)處理,很快就會靡爛。反正爛命一條,趙元朗並不惦記這個,只艱難地喘息著,氣若游絲地握住趙炅冰涼的手,緩緩道:「光義……睡吧……翌日還要早朝。別……累著。」
雖說第一次做就把哥哥操射,滋味妙不可言,可見到趙元朗雖不在刑室內(nèi),仍成血人,猶記唐識幾曾叮囑過不可再動刑,然而皇兄看上去好像是快薨了,趙炅方覺自己玩得太兇,大感不妙,往門外叫了聲:「夢佳!」
「奴才在。」夢佳立刻進(jìn)房,見到趙元朗那模樣當(dāng)真生不如死,臉都不敢抬,只拜倒在床下。
趙炅果斷道:「傳唐識幾來。」
夢佳面露為難,恭謹(jǐn)回道:「稟皇上,李太師家守喪,唐太醫(yī)不能來啊。」
趙炅雖知道其他人的醫(yī)術(shù)不好說,也只得說:「今夜太醫(yī)院誰輪值,傳來就是。」夢佳得令後離去,遵旨同時(shí),沒忘了去別處通傳某人。
初次承幸的這一晚很漫長,宛若酷刑。房裡沒有潤滑的膏藥,趙元朗差點(diǎn)去了半條命;不過捫心自問,趙元朗也覺著自己並不配得到更好的對待。
自己從來都不是個好人,他一生中只愛過兩個人,可那兩個人他都虧欠;既知這點(diǎn),想來,也到了他該贖罪的時(shí)候。
他睡醒時(shí),趙炅人已去上朝了。
皇帝打算把宮中所收藏,董源畫的《龍宿郊民圖》,還有巨然所繪的《層巖叢樹圖》給李從嘉作陪葬,只因這兩幅都是南唐舊物,李從嘉生前也曾表示喜歡;但是趙譜公然反對,說這兩幅畫的正本燒掉不行,若能請宮中畫師畫份臨摹本就可以。
趙炅坐在龍椅上,懶懶地說:「丞相,比那兩幅好的,宮中不是還有許多?給太師燒贗品陪葬,豈不是太不給李太師面子?」
丞相趙譜卻打算與皇帝老爺子據(jù)理力爭,他雙手拿著笏板,朝趙炅恭謹(jǐn)?shù)匦卸Y道:「回稟皇上,李太師既然愛惜這兩幅畫,定然也希望後世之人能看到;若是這兩幅畫就這麼隨他一同殯天,宮裡就再也沒有其他南唐畫作。其餘南唐舊畫早已流散戰(zhàn)火之中,李太師又如何會捨得南唐再沒有半點(diǎn)字畫流傳千古,錄於青史呢?」
趙炅還在金鑾殿裡與趙譜鏖戰(zhàn)時(shí),卻聽閣外有人喊聲:「太上皇。」趙元朗聽這聲音耳熟,縱然使盡力氣,也只能微聲回道:「進(jìn)來。」
是四喜,還帶著一位面生的太醫(yī)。
見趙元朗一側(cè)琵琶骨的傷口因著昨晚的情事已然迸開,骨頭森森可見,一攤血流了滿床,雖曾醫(yī)治,留下乾涸的藥粉痕跡,然而傷勢不但不見好轉(zhuǎn),反而發(fā)白、發(fā)黃、靡爛,分泌著體液;下體亦是沾滿精漬與發(fā)黑凝固的血斑,眼前情狀令四喜的心裡難受得慌。
那可是曾經(jīng)的九五至尊啊!怎會淪落得這般地步?若自己晚來幾日,趙元朗怕是得被折騰至死。
四喜潸然落淚,頻頻搖頭,「皇上好狠的心,親兄弟怎至於如此呢?嗚嗚……」
面前的四喜哭得很是動情,趙元朗默然不語,只忖:『此處頗為隱蔽,不想四喜能找到這裏,還能躲過外頭把守的宮人順利進(jìn)入,不愧是他。』
像是看出趙元朗心中疑惑,四喜收拾諸多複雜情緒,向趙元朗請安行禮,隨後跪到床畔,扶著趙元朗坐起身,「太上皇,奴才思您甚久,很是牽掛!見到太上皇您還活著,真是比奴才的孫子中舉人還開心哪!太上皇,奴才一天沒見到您,那真是食不甘味,但是只要您還活著,什麼事都是好事!」
也虧得自己已不再是人君,四喜還能這麼惦記他了。趙元朗點(diǎn)點(diǎn)頭,摸摸四喜的宮帽,讓他繼續(xù)說。
四喜淚眼潸然道:「春長、夢佳無愧偺們之間師徒之誼,助奴才甚多。春長那小子……自從奉命送御酒給李太師以後,便日夜心裡不安。昨夜夢佳去找他,在得知您竟然被皇帝……被皇帝如此對待後……」說到這裡,不由再度垂淚,濕了衣襟。
趙元朗知道四喜是顧念舊恩,但自己也不過就是被親弟弟操了一次屁股,損失顏面,兼之亂倫,傷害都比不上穿琵琶骨還有挖掉手腳筋要來得大。
此身既敗如殘柳,他也早已麻木,遂溫聲安慰道:「四喜,你哭甚麼?我人還活著,等死了要哭再哭,你接著說。」
四喜這才用袖子抹抹淚,腆著老臉繼續(xù)道:「也虧得李太師感化,春長這小子向來心狠手辣,心眼子剖開來都是黑的,不知作過多少壞事,居然也能良心發(fā)現(xiàn),幫了奴才這個大忙!」
「若非有春長帶路、支開其他內(nèi)侍,奴才在宮中無權(quán)無勢的,豈能趕到太上皇的身側(cè)服侍?想來太上皇的身體也不如往日,奴才便帶了鄭太醫(yī)來協(xié)助。」
就是自己到如今境地,李從嘉已死,都還能以這般方式襄助他。確實(shí)厲害。
想到這裡,雖說心中酸楚,趙元朗仍寬慰一笑,隨後便歛起神色,「我雖謝你,可你就是來了,或者你帶了一個太醫(yī)來,我也走不脫。」
如今的他只有一個心願,那就是去見李從嘉最後一面。然而有身上這副手腕粗的鎖鏈在,他愣是出不去。
那太醫(yī)驀然發(fā)話道:「稟太上皇,把鐵鉤從琵琶骨裡頭拔出來,不就得了?」
趙元朗聞言不解,只因唐識幾曾要緊地囑咐過:『若拔出這兩把鉤子,登時(shí)鎖骨盡碎,筋脈斷裂,太上皇,不出一日您必然要薨。』
鄭太醫(yī)竟然這麼說,不是蠢,就是壞。
今日已是李從嘉停靈的最後一日,而皇帝結(jié)束早朝後,很快便會來望他。若被他發(fā)現(xiàn)四喜帶了太醫(yī)過來,屆時(shí)連同四喜都會有難。
這一對穿過琵琶骨的鉤子,是拔,還是不拔?
──茍活,還是求死?
為了李從嘉,當(dāng)下,趙元朗總得有個決斷不可。
三月:(謝新恩)
(二十八)偶緣猶未忘多情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xù)處。那日夜思念、盼望入夢的趙元朗終究是薨了。
曾憶兩心相許的乞巧宴、不堪受辱的初次承歡;自己病中時(shí),帝王那溫涼而厚實(shí)的掌心;對鏡簪花時(shí),郎君在身後熾熱又滿懷情意的懷抱;出宮彈琴時(shí),如高山流水般的一人撫琴、一人側(cè)耳聆聽。
曾被皇上奪去摯愛妻子,亦有在玉英閣留宿時(shí)夤夜的索求與歡愛;福寧殿中偶一為之的狎邪與自己的不屈。
吳越國主來朝時(shí),那曲令自己被打入天牢的〈浪淘沙〉;多疑的君主對自己的不信任與無情;還有最後那一聲聲已然無益,卻仍牽動己心的「對不住」……
那些個浮浮沉沉的往事,思來雖全是痛楚,倒也熱鐵烙膚、刻骨銘心。李從嘉是恨趙元朗,倒也不能說是全然的恨;他曾懊悔自己為何要拋卻故國,甘心來到汴京作降虜;而今思來,竟已全然不悔。
心愛之人與他的來日都已全部折戟於此,成了宮牆下黯淡的餘灰,琉璃瓦上點(diǎn)綴的浮光。
李從嘉生發(fā)感觸,不覺間細(xì)聲道:「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jīng)百千劫。常在纏縛。」
是了,情想合離,更相變易,皆因業(yè)感多少而受果報(bào)。
過去在故都金陵,李從嘉曾與周嘉敏跪在佛堂裡禮佛,他心裏問著:佛祖,為何您不願庇護(hù)南唐,卻要讓大宋強(qiáng)盛,幾乎一統(tǒng)天下?
那時(shí)生即是苦、眾生平等的道理,他還不懂;而今他已懂了。
李從嘉思忖間,動了心,「噗」地一口吐出血來。
唐識幾見狀,忙去探他脈息,既看出來了,遂扶著李從嘉,殷切道:「太師切勿再傷心勞神,太上皇不是要您好好地……」李從嘉知道唐識幾雖先給他服過解藥,然而牽機(jī)究竟是入體的,否則恁地適才自己竟咳出黑血來,四肢百脈都發(fā)酸?
他望著唐識幾,問道:「識幾,告訴我,我是否已然命不久矣?」說時(shí),眼底沉定如古井水,不起波瀾,已不將殘軀放在心上。
李從嘉說的自然不錯,可唐識幾不捨得說出實(shí)情,一逕地說:「太師,甚多思慮對您的病體有害,您別想這些。」李從嘉搖搖頭,「飲過牽機(jī)未死,就是活罪也難逃。」
唐識幾聞言蹙眉,很是傷心,卻只能一味安慰:「太師懷璧其罪,可為何懷璧是罪?微臣可以帶您……帶您……」他想說出「離開」二字,可李從嘉的病體能否撐持住?自己是否有能耐護(hù)他脫離御林軍的追捕?唐識幾心中無絲毫底氣。
李從嘉瞧出他纏綿情意,溫婉一笑,懨懨道:「識幾,我很感謝你。但是輾轉(zhuǎn)於一人手心,生死全由皇上,我倦了。既然命不久矣,又為何要繼續(xù)撐持?」
「人終有一死,或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他微微一嘆,「我比鴻毛更輕。」
唐識幾道:「太師,您未來必將青史留名,又何苦如此自卑自賤?」而今李從嘉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模樣,著實(shí)令他心中酸楚。
已無所愛之人,便無所謂活著──他自是理解李從嘉的感受,可他呢?為何李從嘉不願意哪怕為著他,再多活些時(shí)日也罷?
李從嘉見壽材仍在,而今一死,時(shí)候正好,不必勞動太多人,當(dāng)下命解頤:「將案上那盅酒遞過來。」解頤知是春長送來的牽機(jī),一時(shí)未動。李從嘉又看向墨池,墨池會意,終於乖順地捧過酒壺遞上。
唐識幾當(dāng)下想將酒壺打翻,李從嘉護(hù)住,對著他悲絕道:「我但求一死,以了明此債,識幾,若你真的愛我,疼我,就不要阻攔我……不要再讓我苦得更久。」
一時(shí)間想到李從嘉就是未飲牽機(jī)前,也是日復(fù)一日地咳喘,每回都見血,幾乎耗盡他所有的精氣。李從嘉已人比花輕,彷彿一張薄紙,再經(jīng)不起一點(diǎn)風(fēng)吹雨打。強(qiáng)逼著他吊命,就是真的為他好麼?
一瞬思慮,他方微怔,李從嘉竟已就著壺嘴,將壺中剩餘的酒盡皆飲入。人生在世如春夢,我且開懷飲數(shù)盅。不久時(shí)他便面色酡紅,狀似微醺。溢出的酒水淋漓撒在衣衫上,透出晶瑩膚色。酒過愁腸,人至少是高興的。
「太師!」唐識幾忙奪下壺摔在地上,可壺裡已一丁點(diǎn)毒酒都不剩。他拍李從嘉的背,可不論怎麼吐,都只是一地殷紅鮮血,在靄靄白雪中格外刺目。
藥性很快發(fā)作,李從嘉開始抱著隱隱作痛的肚子,蜷縮在倒臥的趙元朗懷中。他強(qiáng)忍毒性,抬起沉重的眼皮,想再一次看清趙元朗的容顏。
鵝毛般的大雪已將玉英閣凍作透明,雪沉沉積壓在趙元朗纖長的睫毛上,抑或是自己的視線開始模糊,竟幾欲看不清他本來俊秀的面容。
就是再冷,都不比那逐漸僵硬的屍身在眼前被大雪掩埋,更令人猶覺刺骨心痛。
「元朗……」毒性逕入四肢百骸,再多話語到了唇邊都已支離破碎。心知死灰本就無法復(fù)燃,李從嘉不覺間收緊臂彎裡那人。
你我此生既然曾經(jīng)同淋一場雨雪,又能否算得上是……共白頭?
淒然一笑,他亦知道這念想只是癡。
李從嘉本是金陵人氏,向來怕冷,唐識幾不要他就是到死,都冷冰冰地倒在雪地,遂除下毛氅,覆在李從嘉身上,長跪在他身側(cè)護(hù)持著。
見他奄奄一息,唐識幾知道李從嘉終究是選擇離開他,噙著淚,微微喊他兩聲,「從嘉,從嘉……」
死前還能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恍若趙元朗,恍若他的父皇李璟、皇兄弟李弘冀、李從善,這一聲「從嘉」令他心裡一暖,很是欣慰。
「識幾,你……永遠(yuǎn)、都是待我最好的。」
螓首微抬,李從嘉感激地望著唐識幾,勉力抬手,撫上那人已被雪水打溼的冰涼的臉,「我死後……別繼續(xù)待在宮裡,好好、活著……」
「……本是我……配不上你。」李從嘉用盡最後力氣,握著他的手,櫻唇輕啟道:「出去找一房……好的姑娘……成家立業(yè)……」
唐識幾縱然對著李從嘉有萬千掛念與不捨,卻也心知花開花落自有時(shí),終究是對著他堅(jiān)定地點(diǎn)了頭,「從來就沒有甚麼配不配得上。今生得以伺候您,本是微臣天大的福氣。」
李從嘉墨色眸光黯淡,意識漸行漸遠(yuǎn),最後的多情一瞥落在唐識幾悲慟得眼眶含淚、神色慘澹的姿容上。
他清俊儒雅,本該大有前途,只可惜為自己所累,攤上這唱不完的悲歡離合。願他此後生生世世,永不入這令人厭倦的宮闈。
「識幾……答應(yīng)我……」
他情願相信在自己走後,唐識幾必然會過得很好,不會讓自己失望;李從嘉微微一笑,不及說完,便在碎裂般的痛楚中停止了呼吸。而他這一生大抵是場南柯一夢,於夢醒後化作一縷輕煙,甚麼都握不住,也留不下。
李從嘉本是最怕冷的,如今卻死在這大雪中。漫天的白雪皚皚。看著李從嘉依然清麗,宛若安睡的屍首,唐識垂下纖長眼睫,心裡像是被成千上百的大石堵住,有口難言,心悶難解。
他終於是被最在意的那人,遺留在這亦無甚掛念的人世間。
──太師,得與您心愛之人偕行九泉之下,也算是得償所願。臣是羨慕您的,也羨慕太上皇。臣羨慕你們……
唐識幾不捨地來回?fù)徭吨顝募瘟粲叙N溫的屍身,聲音顫抖著在他已被凍紅的耳畔呢喃,如若那已闔上雙眼之人能聽見似的。
「太師,皇宮配不上您,人間配不上您,這場雪也配不上您。」
唐識幾不知是在說給誰聽,許是李從嘉,或是自己;許是這刺骨到令人生厭的凜冽朔風(fēng)。
在他眼裡,李從嘉本是不染凡塵的天上謫仙人,汴京宮牆內(nèi)肅殺、壓抑的風(fēng)雪,怎堪配沾染他的玉身。
遙仰風(fēng)華,唐識幾腦海中所有的記憶,全停留在遇見李從嘉那一日;或許陽光不甚明媚,宮牆依然斑駁。
他本是個最普通的太醫(yī),素日裡都在後宮幫娘娘們望脈、保胎,早已厭倦妃嬪們之間的爾虞我詐,直到一次偶然,得以入玉英閣中為那倦世之人醫(yī)治。
自此,他成了他一個人的太醫(yī)。只有自己知道他的病體,也只有自己才能照顧他,他本深信自己能做得很好;卻不想還是迎來這一日。
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大抵如是。
李從嘉從不俯視他,直將他視作心裡人。同床共被的那一晚,已是他這輩子最美好的時(shí)刻。
唐識幾一生中未曾識得悸動,只緣這一次的動心,足矣。
猶記一聲聲多情的「識幾」,他流轉(zhuǎn)的眸光,溫涼的指尖,染就詞牌的鮮血,鴛被裡的溫度與貼體的碰觸……
唐識幾此生能回報(bào)的,唯有生死相隨。
末了,低低一聲:「太師,微臣來陪您。」唐識幾拾起壽材旁的刀,刀鋒摁在自個兒白皙的頸間,往下一按,鮮紅的血液噴濺而出,飛濺在發(fā)喪的白幔上。
那一刻,雪停了,玉英閣重歸寂靜。
《小劇場》
其他下人:太師您已死了三個小時(shí),怎還不薨呢?????
解頤:暖爐呢?想進(jìn)去烤手。
墨池:肚子餓,外面冷,腿痠。
唐識幾:Where is my 雞腿便當(dāng)?
元朗:我背很冷,腰有點(diǎn)痛。還得躺多久?
從嘉:下戲沒?想卸妝,拔隱形眼鏡。
四月:(古代美人把我養(yǎng)成替身)
(四)人死不能復(fù)生
這事對我而言倒是好處多多,過去那個被人約到?jīng)]人的地方,然後被一把抱住的人通常是我。白隱心來了以後,我就不用整天被男人抱了!
下課時(shí),白隱心終於回到教室。
我對著他,「欸。」
「?」他吸著可爾必思,看著我。
「上一節(jié)課,在操場被抱的那個人是你吧?」我說。
他持續(xù)吸著可爾必思,點(diǎn)點(diǎn)頭,好不容易才放下飲料,「怎麼了?」
「你怎麼沒推開那個人?」我問。
「為什麼要推開?」他回答。
「你喜歡那個人嗎?」我又問他。
「沒感覺。」他說。
「那你幹嘛不推開他?」我再問道。
「這無所謂,」他回答:「我不在乎。」
「啊,可是對方會在乎吧?你有好好地跟對方說你不喜歡他嗎?」我問。
他點(diǎn)了頭。
「怎麼說的?」我問。
「我距離洞虛期還有七百多年,這些日子不能起心動念。」他說。
……你是《飄渺之旅》看多了吧?好想打他啊。
可是想到他剛才好像真的有什麼能為,我不由得問:「你是修者,真的假的?」
他點(diǎn)點(diǎn)頭。「你也是。」
我也是?「修什麼的?」我問他。
「玄修。」他說:「你是煉神者,以氣為食,能窺人星宿,探萬世之奧祕。」
「那是修什麼的?」我問:「你可以說現(xiàn)代中文嗎?我聽不懂。」
「你已經(jīng)辟穀了,原本境界還能更高。」他露出一個饒有興味的眼神,「想知道?」
這傢伙好像對這種亂七八糟的話題特別有興趣,表情終於有點(diǎn)人味。我點(diǎn)頭,「你別賣關(guān)子,倒是說啊。」
「這不好說,你自己看。」他比了個劍指,沒等我反應(yīng)過來,就把凝光的兩指抵在我的脖子上。
一時(shí)間,我打了個冷顫,飛快看見許多不同的景象掠過腦海;與其說是「看見」,不如說是「感受」到。
我看見長得千嬌百媚、婀娜多姿的……穿著天青色道袍的,我自己?
也看見了白隱心,當(dāng)時(shí)他還不穿學(xué)校的皮鞋和西裝褲,裡頭那件黑色的銀繡背心倒是沒換。
現(xiàn)在的他看起來比記憶裡還要更年輕,由不得我去懷疑,修仙能讓人變年輕是真的。
他是「天罡門」的大師兄,跟其他師弟們比起來,比較勤於練武,所以通常有人來找碴的時(shí)候,負(fù)責(zé)阻止桌子被掀的人都是他。
以前我們讀的神訣是《紫微星宿經(jīng)》,主要使的道法是「星道」,也就是所謂的「煉星之術(shù)」,最早創(chuàng)立的祖師是姜太公,同門的有名人士有劉伯溫,他的《燒餅歌》就是利用這種異能寫出來的。
不像別的劍仙整天出去跟人打架,這個門派好像全部都是宅男,手不動三寶,無縛雞之力,整天待在洞裡看自己的未來、別人的未來、世界的未來,掐指一算,就覺得自己點(diǎn)破天機(jī)、超脫紅塵。
雖然我形容得很白癡,但事實(shí)上,天罡門曾經(jīng)出過不少國師,除了劉伯溫以外,還有張良跟諸葛亮。
雖說他們身負(fù)異能,但是這也並不代表修者就能挽大廈於將傾,畢竟能被看見的未來,都是早就註定好的,這也包含了人在看見未來以後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即使如此,人卻往往想追逐如何去預(yù)知未來,未來是理型,是完美的定數(shù);是不完美的、時(shí)時(shí)變動的現(xiàn)象界的人最深層的渴求。
我忽然明白隱心的意思,為什麼他沒推開那個人?因?yàn)樗静辉诤酰呀?jīng)不在乎別人對他的情感,甚至他自己的情感都開始變得淡薄。
我感覺這無窮盡的意識中所蘊(yùn)藏的訊息量非常大,我待在其中的時(shí)候,時(shí)間是不會流動的。我肆意撥動這一大批記憶中的時(shí)間線,感覺自己能融入任何時(shí)候,像空氣一樣潤物無聲。
問世間誰人無憂,唯神仙逍遙無憂。我想看什麼、知道什麼,我就能辦到,我是隨心所欲、超脫於物理法則的。
我一一地貪看那些「尹朝晴」的前世,直到看見師尊突然把我的袍子撕個粉碎,摁倒在床上的時(shí)候。
師尊相中我的體質(zhì),想要我的能為,於是想將我作為爐鼎。
白隱心搶進(jìn)房,一個彈指射死了他。與此同時(shí),師尊笑道:「為師得不到的功力,你也不能要!」他的劍氣擊穿我的天靈蓋,「唔……!」我的元神雖然想出竅逃生,奈何修為不足,魂魄很快就灰飛湮滅。
「──小晴!」白隱心也察覺了這一點(diǎn),他當(dāng)下的難受、痛苦幾乎完全傳遞給我,可就算殺了一萬個師尊,已經(jīng)被擊碎天靈的那個人也不會活過來。
「同門相愛……本是逆天而行……」師尊流出血淚,痛苦抽搐著,口裡一甜,「你永遠(yuǎn)不會……與你真正愛的那個魂魄、重逢。」
白隱心聞言臉色一變,他知道師尊的修為,所說的話是讖語,此話不假。儘管如此,他卻打從心底否定。
他用力地抱住我的屍身,「胡說!655年以後,朝晴歷完劫,他會重生!他會投胎轉(zhuǎn)世!」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yàn)樗浅G逦乜匆娏恕?/div>
「我可以等!不論多久我都等!以前我不在乎能否長生,可從今天開始,我之所以長生不滅,只為了等他一個人!」他流淚道。
師尊卻猖狂一笑,「無知!那不是他……那不是你愛的那個人……等多久都是無益……咳咳!」
「什麼意思?誰要奪朝晴的舍?」白隱心猛地掐住師尊的領(lǐng)子,拎起他。
「人死……不能復(fù)生……噗──」師尊的話才說到一半,就吐了白隱心滿臉血,而後嚥下最後一口氣。
「人死不能復(fù)生?為什麼?投胎以後不就復(fù)生了麼?」儘管彼時(shí)的白隱心已屆分神期,能操縱自己的元神去窺探天地間的奧秘,卻還是不願意承認(rèn)這個真理。
──人死不能復(fù)生。就算同一個人投胎轉(zhuǎn)世,那個已經(jīng)投胎的人,也不會是他真正想要的那個人。
在這之後,白隱心因?yàn)橥T師兄弟們的追殺,開始隱姓埋名地生活。儘管其他門人的武功都非常菜,六、七個人圍不住他一個人,他卻不想傷害同門,同時(shí)也是因?yàn)椴幌朐鞓I(yè)、損修為。
他將師弟的屍體埋葬以後,曾跟隨鄭和出海,到麥加朝聖,兩人一起進(jìn)入卡巴天房;穿一襲白袍,與貝都因人們一起在沙漠裡煮豆子吃。也在明思宗自縊後,到老歪脖子樹下,替他上了最後一炷香。
虎門銷菸的時(shí)候,他因?yàn)橐呀?jīng)預(yù)知接下來全國會禁菸,所以進(jìn)鴉片館抽了生平最後一口菸。
歷經(jīng)滿清入關(guān)、立憲運(yùn)動以後,他居然一路活到現(xiàn)在,超過六百年。
溥儀在馬路上騎腳踏車的時(shí)候,按鈴要皇帝讓路的那個人,是他;溥儀想進(jìn)去已經(jīng)被圈起來賣門票的養(yǎng)心殿時(shí),一道劍氣把圍住大殿的紅布條射斷的人,也是他。
他白隱心,居然這麼厲害?
……
唔……!
我本來想繼續(xù)看下去,卻忽然感覺頭痛欲裂,難受得不行。
我感覺整個人都快要被扭曲、撕碎。我好像隨時(shí)會在這個所有事件都交雜在一起的異空間中化為一粒塵沙。
隱心、隱心……快點(diǎn)、快救我……!
『你看的東西已經(jīng)太多,我必須幫你消去一些,否則你會撐不住。』恍惚間,我聽到白隱心的聲音,『我的事與你無關(guān),你不必全然知道。我知道你的事就好。』
一道眩目的白光淹沒我腦海中所看到的一切景象。我感覺整個人搖搖欲墜。
「朝晴他怎麼了?!」我能聽見成颯心急的語聲,卻動不了。
「我?guī)ケ=∈摇!拱纂[心回答他。
「老師也跟你一起去吧?」成颯說。
「不必。」白隱心說完,我只感覺整個身體都輕飄飄的,能聽到同學(xué)們的驚呼還有竊竊私語:「力氣真大!」、「公主抱耶,好羨慕。」
我能聽見有力的、有序的,令人安心的心跳聲。一雙溫暖的大手捧著我,不論如何我都不會被落下。
而後我就失去了意識。
五月: (韓粉)
關(guān)於我男友(又)跑去力挺韓國瑜選總統(tǒng)這件事(?)
邵又青一直覺得,浩男是韓粉這件事,應(yīng)該從頭到尾都只是為了惡整他而編出的笑話;直到浩男他一聲不響地去了臺北。
灰色與青:阿男,你人在哪裡? (既讀み)
灰色與青:你回個訊息好不好?喂! (既讀み)
【灰色與青-語音通話來電中】
《接通》 《掛斷》
【對方暫時(shí)無法接聽】
【未接來電】
「──他到底去哪了啊!!!」
雖然手裡握著Switch Pro的手柄,眼睛盯著電視螢?zāi)唬墒巧塾智噙B初始空島都沒有出;他男朋友已經(jīng)上臺北兩天,不回訊息,不接電話,這讓他很焦慮。
他不習(xí)慣阿男不看訊息,不回訊息,不發(fā)他看了也不想回的垃圾訊息,諸如「你午餐吃了沒?」、「吃了啥?」、「今天工作忙嗎?」的日子。
邵又青在他哥買的無印良品小沙發(fā)上打滾,蹂躪他寄養(yǎng)在這裡的IKEA鯊魚,「阿男平常還是挺乖的,尤其我們交往之後,他收斂不少,可是到底為何一聲不響跑走?」
「你看這個是不是他啊?」方宇直把手機(jī)遞給邵又青,同時(shí)替他按下手柄上的「+」鍵,暫停了薩爾達(dá)。
邵又青接過Samsung,滑了滑。
「韓粉群聚國民黨部,力挺韓國瑜選總統(tǒng),要求黨中央辦初選」斗大新聞標(biāo)題映入眼簾。
「???」邵又青很困惑。雖說這群韓粉的行為本身就挺令人迷惑,但他困惑的是另一點(diǎn)──在他們交往之前,浩男曾跟他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真的不是韓粉。若不是浩男這麼說,他是絕對不可能答應(yīng)跟浩男交往的。
然而往下一滑不得了,第一張附圖裡頭,他就清晰看見他男朋友;雖然戴著印中華民國國旗的白底紅邊鴨舌帽,還有黑口罩,可是陳浩男就算是燒成灰,他都認(rèn)得。
大熱天的,他卻氣得渾身發(fā)抖,從腳心一路冷到腦門。邵又青一時(shí)間覺得這張照片的內(nèi)容,將成為他今晚的惡夢。
「那是Otoko吧?」方宇直用手指指著那個看起來好像是想隱藏在人群中,可是因?yàn)橹茉馊际谴笫濉⒋髬專灾领犊雌饋硖^年輕、違和感十足的俊朗青年。
「朱立倫!脫魔戒!朱立倫!脫魔戒!」新聞附的影片裡,浩男穿著一身黑底T恤,胸前斗大三個字「KMT」,跟其他人一起舉起拳頭,激情喊話:「國民黨!徵召初選!」
「小青,別丟我的手機(jī)!」就在邵又青像是看見髒東西,差點(diǎn)把Samsung丟掉時(shí),方宇直摁住他的手,「我工作也不容易的。」
「朱下韓上!唯一支持,韓國瑜選總統(tǒng)!」影片裡,浩男還在跟著其他人一起大聲嚷嚷,更糟的是──他帶了他的IKEA小鯊魚上臺北。
讓小鯊魚一起跟著喊「朱下韓上」,簡直是虐待動物的行為,動保團(tuán)體也該管一管了吧?!還不如把那條鯊魚放生IKEA!是可忍,孰不可忍?
「嘔……!」邵又青見狀,差點(diǎn)把自己剛吃的八方雲(yún)集鍋貼吐出來。
方宇直替他按下停止鍵,「覺得不舒服就別看了。等活動結(jié)束之後,他自然會回來。」
「他也已經(jīng)二十四歲了,你總該讓他有點(diǎn)私人空間?他一聲不響跑去臺北,又不聯(lián)絡(luò)你,這點(diǎn)確實(shí)是他的不對,可是你讓他盡情去抒發(fā)對……對韓國瑜的愛意(?),他玩夠了,也許就回來了?」
方宇直說道,儘管他說的時(shí)候也充滿遲疑,這點(diǎn)就連又青都能感受到;但是因?yàn)樗呀?jīng)很了解陳浩男這個人了,反而覺得邵又青有些小題大作。
「他如果是上臺北跟beetalk裡的帥哥約砲,或是去陪老女人吃飯賺外快,這也就算了──可是、他是去幫韓國瑜應(yīng)援,支持韓國瑜選總統(tǒng)欸?!你能忍受你男朋友那麼腦殘嗎!」邵又青抓住方宇直的衣領(lǐng)搖了搖。
方宇直別過頭,「抱歉,阿青,因?yàn)槲夷信笥阉腔M(jìn)黨的,所以我真的沒辦法體會你的感覺。」
「……」邵又青放下猛然攥緊方宇直衣領(lǐng)的那隻手。
是,因?yàn)閯e人的男朋友沒有他的男朋友腦殘,當(dāng)然無法體會他的痛苦;可是跟這種腦殘交往的自己,難道不也是個低能兒嗎?
邵又青曾無數(shù)次思考過這個問題──他到底後不後悔,三年前自己選擇的那個人是阿男,而不是小宇?
時(shí)光飛逝,他們已經(jīng)在一起三年;撇除得不到的東西永遠(yuǎn)最香,小宇成了印在他心口的硃砂痣這個因素以外,又青本來一直都覺得阿男其實(shí)也不差,不然他們不可能一週最少打三次砲,三年了都沒變。
至少……若要論起唯一的、最大的優(yōu)點(diǎn),那就是浩男很能夾他,總是能把他夾到射出來。他在床上的表現(xiàn)很喜人。
可就在韓國瑜捲土重來,阿男專程跑到臺北去應(yīng)援韓國瑜選總統(tǒng)之後,他不再覺得浩男這個人瑕不掩瑜,於是這個問題再度浮上他的心頭──
他很疑惑自己到底當(dāng)初是怎麼豬油蒙了心,才會跟這個人交往的?還一睡就是三年!
想到自己居然睡了三年的韓粉,又青頓時(shí)覺得自己的雞雞髒了、不能要了!
哪怕浩男的身材再好,臉長得再好看,整個人再怎麼符合他的性癖;只要這個人是個韓粉,就代表他智商有問題,絕對是OUT!
「小宇,我……」邵又青反覆想著,要是自己當(dāng)初是和方宇直交往,而不是陳浩男該有多好?他望著方宇直,思來想去,心底最深處的渴望並沒有出口,最後說的是:「你陪我去臺北找浩男,好不好?」
就連阿男的不告而別,都成了他想拿來和方宇直一起外出約會的藉口。
以前的方宇直鐵定想都不想,就算要跟公司請假,也會答應(yīng)幫邵又青的忙;如今的他卻多了很多思忖。他問:「你打算現(xiàn)在就去臺北找他?」
兩天了,是該去找人了,不然萬一阿男想不開,最後喜歡韓國瑜、喜歡到去找他獻(xiàn)臀求操怎麼辦?就算人家韓國瑜不答應(yīng),他也不想看見陳浩男淪落成失足青年啊!
邵又青還是頗為擔(dān)心,「嗯。」他沉痛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
聞言,方宇直對著他弟泛出一個苦笑,「小青,真的很對不起,可是現(xiàn)在不行,今天也不行,晚點(diǎn)我還要去柏融家吃飯。明天的話或許可以。」
「噢……」那是他哥交往三年的男朋友,嚴(yán)格說起來算是……嫂子?大舅?
是個很好的人,不過邵又青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長得很像3Q哥,雖然比3Q哥更帥、更年輕。
『他們都已經(jīng)論及婚嫁了……交往得也很穩(wěn)定。』
想到這裡,邵又青有些失落,只得盡可能隱藏自己的情緒,對著方宇直強(qiáng)扯出一個笑容,「哥,我也在這裡打擾你很久了,我在晚飯前離開吧。等等我就騎車去車站上臺北找人。」
「你要怎麼找?你有他的手機(jī)定位嗎?」方宇直說道:「都快晚餐時(shí)間了,你跟我一起去博融家吃飯吧,他們都知道你是我弟,帶你去也是正常的。」
然而只有邵又青自己心裏清楚,雖說小3Q哥從來沒對他表達(dá)過芥蒂之情;自己人生中最大,且至今仍未實(shí)現(xiàn)的遺憾,卻是從沒操過宇直,或者被宇直操過。
他對自己的乾哥哥懷抱著一點(diǎn)都不假的戀慕之情,哪怕他們都已經(jīng)有了各自的男朋友;儘管如此,他卻捨不得斷絕與方宇直之間的聯(lián)繫,只因?yàn)榉接钪笔冀K對他很溫柔、很有耐性……像是把對全世界的耐心,都給了他這個作弟弟的。
這讓邵又青很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那是一種和對著阿男絲毫並不相同的情感。
「……」想到這裡,邵又青覺得自己不該一錯再錯,總是看著碗外的,不屑碗裡的。
哥哥很好,比什麼人都好,這點(diǎn)他知道;但是浩男也有浩男的好,否則自己當(dāng)初不會和他在一起。
……就算他是個十惡不赦、其罪當(dāng)誅的韓粉。
想到自己的男朋友居然那麼喜歡那個光頭,邵又青頗感髮指,心口都絞痛起來。
「呃……!」邵又青摁住自己的心口,真的痛。
「怎麼了?」方宇直幫著揉了揉邵又青的胸口。
「……阿男他,哪個光頭不去喜歡,為什麼非得要喜歡韓國瑜?蘇貞昌的頭難道不夠光、不夠亮嗎?」邵又青咬牙切齒地說道。
方宇直知道了邵又青的痛,可除了輕聲說一次又一次「對不起」以外,他無能為力。
邵又青喘了口氣。
「先去臺北,總會有辦法的吧?」邵又青整理了心態(tài),苦笑道:「你和博融哥回家一趟也好,我去國民黨總部帶阿男回家。」
「這件事總得有人做,阿男他家人全部都是忠誠國民黨員,再這樣下去,阿男他好不了。」
──原來身為韓粉,是一種病,得治,是嗎?
方宇直並沒有再阻止他,只說:「有事隨時(shí)賴我,真的需要幫忙的話,我會去臺北找你。」
邵又青點(diǎn)了頭,他很感激小宇的心意,可正是因?yàn)橹婪接钪闭娴臅^來,所以並不想麻煩他。
方宇直望了他一會兒,心裡一動,彷彿又看見三年前那個脆弱的邵又青──彼時(shí)的他與現(xiàn)在有相同的煩惱。
方宇直很猶豫,當(dāng)年就是自己鼓勵弟弟和陳浩男在一起,因?yàn)樗吹贸鲫惡颇写_實(shí)很喜歡阿青,也不是個壞人;然而一個人的政治傾向根深蒂固,很難改變。
或許對浩男而言,喜歡阿青、很喜歡阿青是事實(shí),可是想支持韓國瑜去選總統(tǒng)的心情也同樣強(qiáng)烈?所以他無法為了阿青,放下韓國瑜。
換個角度思考,方宇直也認(rèn)為自己的男朋友支持蔡英文,但他並不會因此支持蔡英文,於是他稍微能理解阿男的感覺。
既然如此,那麼自己當(dāng)初的推坑,該不會也是錯的?否則為何在三年後,一樣的事會再度發(fā)生呢?
方宇直往前一坐,深深抱住邵又青,摸摸他蘇打汽水色的頭髮,「小青,這件事哥也有責(zé)任。」
邵又青一把回抱住他哥的窄腰,「沒事,阿男整天搞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習(xí)慣了。」
──對他們二人而言,繼續(xù)在一起,得到更多的到底是快樂,還是互相折磨?
方宇直思量著,垂首往又青的唇角輕輕一吻,「祝你好運(yùn),把Otoko帶回來,讓他不要再繼續(xù)沉迷韓國瑜。」
「……哥。」邵又青把臉埋在方宇直寬闊的肩膀上,「我愛你。」
聞言,方宇直一愣,「我也是。」他低聲回應(yīng)道,一時(shí)間沒捨得放開懷中那溫暖而精壯的身板。
邵又青抱著方宇直,儘管貪戀著溫柔鄉(xiāng),還有他哥身上淡淡的CK香水味,大腦中卻已經(jīng)開始brain storm。
他迷惘,感覺自己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正遭受激烈的挑戰(zhàn),沒想到韓國瑜捲土重來會為他的人生帶來如此劇烈的變化。
是啊,阿男明明可以沉迷hololive、薩爾達(dá)、崩壞星軌、楓之谷、天堂M、買股票、線上博彩,甚至是喝茶吃魚……他可以沉迷的東西有那麼多,哪一樣都比當(dāng)個韓粉好,可為何他偏偏執(zhí)著於當(dāng)韓粉呢?
──我該拿什麼來拯救你?我的韓粉男友。
方宇直並沒有十八相送,不讓他走,而是以「風(fēng)蕭蕭兮易水寒」的心態(tài),欽佩地目送壯士離去,前往本能寺──國民黨黨部。
放下薩爾達(dá),也放下對他哥的依戀,邵又青選擇離開方宇直的公寓,踏上征途。
只見外頭的天空陰沉沉的,還沒到晚上六點(diǎn),天色已經(jīng)黑了泰半。
在將鑰匙插進(jìn)狗狗肉之前,邵又青下意識拿出手機(jī),熟門熟路地快速打開噗浪,發(fā)了一則噗。
【偷偷說】旅人們好,我有一個困擾想請旅人們幫忙心理諮商一下。
Alpaca7878:?
Jujube4747:卡
?_?:我男朋友失蹤兩天,完全找不到人,不接電話,Line只已讀,不回訊息。
Bun5546:Reply @?_?(關(guān)於感情問題,我一律建議分手.jpg)
Pisces3359:噗主有先報(bào)警,或詢問男友的家人嗎?
Turkey2867:卡
?_?:我在看新聞,結(jié)果看到我男朋友出現(xiàn)在支持韓國瑜選總統(tǒng)的誓師大會現(xiàn)場。
?_?:他這兩天搞消失,很可能是為了要上臺北支持韓國瑜選總統(tǒng),可是又不想讓我知道,才會鬧失蹤。
Alpaca7878:Reply @?_? ㄜ,噗主,你知道嗎?雖然有些事情諮商有用,可是有些事情諮商沒有用喔~
?_?:Reply @Alpaca7878 旅人可以提供一點(diǎn)意見嗎?我現(xiàn)在心裡真的好痛苦。當(dāng)初是男友跟我說他不是韓粉,我才下定決心跟他交往,沒想到三年後我才發(fā)現(xiàn),他居然真的是韓粉!!
Turkey2867:挖靠這是詐欺了吧(怒emoji)
Alpaca8787:(扁鵲三連.jpg)治不了,等死吧,告辭了。
Alpaca7878:給噗主一個衷心的建議,放棄治療,立刻封鎖,跟他分手,切斷一切往來。
?_?:可是我們已經(jīng)交往了三年,他人真的很好,長得很帥,工作也不錯,未來可期……我們是有想過要結(jié)婚的。
Pisces3359:心疼噗主,拍拍(抱抱emoji)
噗主,萬一以後你們結(jié)婚,他變成你老公,然後三不五時(shí)人鬧失蹤,你打開新聞,發(fā)現(xiàn)他又在參加韓國瑜的競選活動怎麼辦?難道你要忍受他,直到韓國瑜死嗎?
Pisces3359:韓國瑜很可能在四年、八年、十六年後,還會再出來選總統(tǒng)喔!(狐貍怒眼emoji)
你看看郭臺銘就知道了(茶)每四年一次的總統(tǒng)大選,都是群魔亂舞,這點(diǎn)就沒變過。
Alpaca7878:不要妄想去改變一個韓粉。
(粗體)你覺得能改變,其實(shí)你不能。
?_?:難道他愛韓國瑜,勝過愛我嗎?韓國瑜又不會跟他打砲!
Alpaca7878:你怎麼知道韓國瑜一定不會跟他打砲?
Alpaca7878:醒醒吧,噗主,雖然你可能不想承認(rèn),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
Alpaca7878:其實(shí)你男朋友喜歡韓國瑜,比喜歡你更多?
六月:(非典型追妻火葬場/萬人迷男公關(guān)PUA實(shí)錄)
(二)Royal Salute 皇家禮炮
十年前,他們都是大學(xué)生,成颯、卓楷銳、權(quán)碩彬三人都是商學(xué)院企管系的學(xué)生。
如今,權(quán)碩彬已不記得卓楷銳,就像成颯也覺得卓楷銳肯定已經(jīng)不記得他了,否則又為何會把他當(dāng)成客人來接待呢?他以為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阿銳,我是成颯,還記得嗎?你……」
卓楷銳拿起62年皇家禮炮的瓶子,熟門熟路地剝開外封,打開瓶塞,往自己和成颯的威士忌杯裡倒了1/3杯,「要加冰塊嗎?」他有意無意地打斷成颯的話。
成颯有些洩?dú)猓c(diǎn)了頭。
卓楷銳細(xì)皮嫩肉的文秀的手,拿起小冰塊夾時(shí)手骨在薄薄的白皙皮膚下若隱若現(xiàn),他自冰桶裡為兩人的威士忌杯各自夾了幾塊冰,而後拿起酒杯,向成颯敬酒,「謝謝你點(diǎn)我,小颯。」這一瞬間,成颯感覺卓楷銳其實(shí)並沒有忘記他。
成颯拿起酒杯,與他碰了碰,兩只杯子之間發(fā)出清脆的響聲,
權(quán)碩彬見方才還無所事事、是事芳心可可的成颯,模樣一變,不但與那位剛來的男公關(guān)熱絡(luò)地聊起來,還互相敬酒,一時(shí)間有點(diǎn)坐不住。
「小權(quán),我老婆打電話來查勤,我先出去買單。」程老闆拍拍權(quán)碩彬的大腿。
意識到或許是自己放太多心思在方蔓蔓還有成颯的身上,以至於怠慢了公事,權(quán)碩彬在程老闆臨去前,問了聲:「程大哥,你覺得有機(jī)會也跟立昀科技合作嗎?」沒放棄幫成颯牽線的機(jī)會。
「有機(jī)會的話都可以啊,只是你那朋友的資歷,應(yīng)該沒你豐富吧,」程老闆沒把話說死,可權(quán)碩彬已經(jīng)聽出異音。
想著至少今天也帶成颯出來見過世面、累積人脈了,其他的強(qiáng)求不來就別勉強(qiáng),於是他舉杯,「程大哥,什麼時(shí)候再出來喝酒?」Richard適時(shí)替權(quán)碩彬添酒。
陪在程老闆身旁的女公關(guān),本來已經(jīng)拿了包準(zhǔn)備送客,見狀默默放下包,也替客人倒酒。
「等Alex有空吧,他不是一週有三四天都來龍亨,他不來我覺得沒意思。」程老闆說道:「下次我們幾個出來就好,你別帶朋友了。」
「好,下次Alex要來的時(shí)候,我打給你。」權(quán)碩彬回答完,便與程老闆碰杯,仰頭飲盡杯中物。
程老闆起身時(shí),權(quán)碩彬作勢也要離座送客,程老闆說:「不必,小權(quán)你坐,難得帶女朋友出來喝酒,玩開心點(diǎn),我回家給老婆交公糧了。」
權(quán)碩彬心說:『死老頭,剛才喝那麼多酒,回家還能硬?』面上仍一派溫和笑容,「程董真的很顧家,還是我?guī)湍憬袀€代駕?」
「不必,幹部說幫我叫好了。」權(quán)碩彬終於送走客戶以後,便兩隻手扠在西裝褲的口袋裡,大步流星地朝成颯與卓楷銳走去。
Richard見狀,拿著兩只杯子,亦步亦趨地跟過去。方蔓蔓則是全程無視他們,自顧自地拿著麥克風(fēng)唱《七情六慾》。
權(quán)碩彬抬手,向卓楷銳打了招呼,沒好氣道:「小颯說,你是我們的同學(xué)?」
卓楷銳沒繼續(xù)坐著,而是立刻起身,向權(quán)碩彬敬酒,「只是認(rèn)錯而已,或許我長得像他以前認(rèn)識的人。」
成颯心想:『楷銳為什麼這麼說?』
不管卓楷銳的回答是不是事實(shí),權(quán)碩彬顯然是滿意的,他露出不屑的笑容,「是啊,我們的母校可是『Z大』,我可不知道Z大有像你這樣的『傑出』校友。」
「如果讀完Z大,還要出來賣屁股,那幹嘛不去讀個●化什麼的學(xué)店就好?你當(dāng)其他Z大畢業(yè),進(jìn)臺灣百大企業(yè)服務(wù)的校友都是傻子嗎?」
成颯聞言,立刻對著權(quán)碩彬搖手,「碩彬,你別這麼說,讀●化的有什麼不對?人家也是家裡有錢才能讀,沒錢的連●化都讀不了。」儘管是反對權(quán)碩彬戰(zhàn)學(xué)校,卻絲毫沒察覺到自己話中的傲慢。
權(quán)碩彬淡淡地瞥了卓楷銳胸前別著的名牌一眼,「Aldrich,」修長的手指敲了敲卓楷銳手中的威杯,「你要跟我喝酒,是嗎?」
「老闆好,」卓楷銳才要上前碰杯,權(quán)碩彬眼神一涼,竟將自己的杯中物全倒入卓楷銳的杯中,「我為什麼要陪你喝?你有領(lǐng)薪水,我可沒有。」
成颯見狀,立刻起身,要去搶卓楷銳的酒杯,「阿銳,別喝,你會吐的。」卓楷銳搖搖頭,低聲向他道:「你別管,這只是小事,我能處理。」成颯這才坐回座位上,望著卓楷銳時(shí),面上卻顯示出倉皇與無助之色。
如此玩命的喝法,分明是蓄意灌酒,卓楷銳猶在遲疑,一時(shí)沒動杯。權(quán)碩彬昂起頭,手指抬著下頷,望著卓楷銳些微發(fā)白,顯然已經(jīng)開始身體不適的臉色,定定地說道:「你是嫌皇家禮炮不夠貴,要82年的拉菲才肯喝?」
卓楷銳心說:『葡萄酒那才是真的吐,威士忌算什麼?』立刻仰頭,把將近一杯的純威士忌一飲而盡,喉結(jié)上下跳動。
黃湯下肚不久,他的腦子就開始昏昏沉沉起來。
見狀,權(quán)碩彬揚(yáng)起嘴角,拿走卓楷銳的威杯,將裡頭的冰塊全倒進(jìn)華麗的垃圾桶,隨後親自執(zhí)起公杯,為卓楷銳的酒杯實(shí)打?qū)嵉卣鍧M,也為自己的酒杯斟滿,只不過是在有冰塊作底的情況下。
「我們乾杯。」權(quán)碩彬拿起酒杯,「Aldrich,你很敬業(yè),今晚很高興能認(rèn)識你。」
卓楷銳笑著點(diǎn)頭,「謝謝老闆,」也拿起酒杯,儘管對著面前這個高大俊俏的金髮男人,內(nèi)心已全是髒話。
隨著濃烈的酒水湧入喉嚨,他的喉管立刻辣燙燙地發(fā)麻起來。
他知道,這兩杯酒已耗盡自己今夜一整晚的扣打,接下來自己少說得休息半個小時(shí)以上,否則會立刻斷片。
──今晚出外勤賺的這錢,是真的虧啊。
卓楷銳下意識忍住嘔吐、咳嗽的衝動,儘管此時(shí)的他臉色早已不能稱得上是好看,看上去也不再那麼地有餘裕。
做這一行,終究是出來給人糟蹋的。